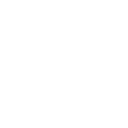天籁之韵与凡俗之美
松铖
天籁地籁人籁,皆是一种声音。天籁当然是很美的,故而,庄子在《齐物论》中借子游和子綦两个虚拟人物的对话,对这三种声音进行了阐释。天籁是高于地籁和人赖的,用子綦的话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其大意为:天籁呵,就是风吹万种孔洞发出的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千差万别的声音是由于自己的形态体质所造成的。因此,天籁是不加修饰的最为纯正的天地之音。由天籁联想到民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民歌是劳动的产物,是群体共同弹拨的和弦,是浑厚与婉约汇聚的情感之韵。民歌从心灵中流淌出来,四散开去,飘逸、弥漫,渐渐发酵成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的人间烟火味……这就是天籁,是民歌的天籁,天籁是最接近本真的东西,因此,民歌绝少斧凿的痕迹。侯红艳的这部《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研究》就是对民歌天籁之美的剖析和解读,全书行文自然流畅,作者以颇具文采的笔触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旬阳民歌在文化进程与现实生活中的美学价值。
“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就着眼点来看可谓高屋建瓴,视角新颖独到。读完全书,通过作者层层剥笋式的分析、论证,我们对旬阳民歌的认识有了更加深刻的领会,换句话说,对整个陕南民歌成长及其生发的环境,在认知上也有了新的启示和发现。旬阳民歌同属于陕南民歌范畴,而最具代表性的陕南民歌还有紫阳民歌、镇巴民歌等,单从旬阳民歌与紫阳民歌所处的环境和孕育的过程考量,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皆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趋同性,这种相似性和趋同性,除了地理位置、气候水文,还有就是相同的历史渊薮的造就,如明清移民大潮的影响,当然,相似性和趋同性,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关系,这就涉及到生态美学的问题,我们说同属于陕南民歌的旬阳民歌,与其它陕南民歌有着完全共通的地方,这即是共性的表现。但这终究只是外在品貌,俗语有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俗。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的作用,“自然生态环境只是外因,而文化生态环境则起主导作用,是它最终把民歌与社会发展、历史交往纳入统一框架内。”那么,即使在一个基本相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但由于文化生态环境有别,民歌的内质也会有所差异,其艺术个性就会凸显出来。个性代表了一种鲜明的文化品格,就这个意义上说,旬阳民歌与紫阳民歌以及其它地域的民歌,虽有相似或相近的地方,但它依然是旬阳的,这是本土熏染的结果,特殊的文化生态必定会为之烙上自己的印痕。
旬阳民歌的原初性即是本土性的体现,但有多少是原初的或者说是本土的,它们能区分出来吗?这当然是徒劳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号子、山歌、小调,在其它一些地方,比如紫阳、镇巴等地,都有相同的艺术呈现,曲牌、内容基本一致。其实这样的情况在紫阳民歌中亦是屡见不鲜。紫阳、旬阳皆是移民区,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互融、碰撞、渗透是显而易见的。紫阳资深民歌研究专家张宣强有一段话说得很形象:“民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树,落在哪里便成为哪里的嘉木,虽有‘桔生南方为桔,生在北方为枳’的现象,但它始终是一棵树,一棵绿树、美树。”因此,即或是外来的,经过漫长的时间磨合,这些南方的俚曲、小调,早已糅化在了旬阳的山水间,落在了田畴和峁梁上,经雨露阳光的滋润,它长成了一棵富有旬阳地域体征和特色的“树”——一棵枝繁叶茂伟岸壮硕的大树。旬阳民歌的发育成长,是内因和外因的促成,侯红艳在《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研究》中,一直强调内因的主导作用: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二者不可或缺,但文化生态环境才是壮大民歌体质、改善民歌基因的给养和条件。生态美学是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这种契合下,精神与物质的依附关系,才会融洽,而美才会折射出凡俗世界的光华。
民歌之美,在我以为就是一种天籁之美。民歌产生于劳动,而早期的劳动,是绝对的肉体与自然的较量,它依靠的是筋骨的强健和耐力的持久,因此,民歌就是在这种苦与乐、悲与喜的挣扎中,情感自觉地宣泄和释放……这种发乎于心的东西,没有人为的修饰,它就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其原初性耀眼而夺目。侯红艳认可民歌这种原初的本色,同时也承认,随着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民歌也在发生变异。时代元素的注入,旬阳民歌的原初性正在减弱,但同时我们又看到,民歌在褪去自身素朴的同时,却又悄然引入了时尚的元素,如民歌与当下生活,民歌与太极城,民歌与旬阳的社会人文关系等等。这或许就是新民歌的一种样态,是继承也是创新。而民歌的原初性还有待于发掘和研究,原初性是不可再生的,如早期的山歌号子、山歌调子以及那些叙事完整的小调、曲子,随着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它们将永远定格在早期的时空中,并成为一种珍贵的时代记忆被储藏起来。
侯红艳笔下的民歌之美,绝无空洞之感。民歌之美就是旬阳的地域之美、山水之美、人文之美,而这些美,它们皆归于生态美学的范畴。美的意蕴深化了、拓展了,民歌从一种单一的曲种,被赋予了新的生命的质量。侯红艳在《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中,紧扣地域文化的脉搏,这是生态美学的入口,也是研究旬阳民歌的钥匙,侯红艳显然是自信的,因为她的表述自始至终从容而又舒缓。旬阳城的自然景观,说到底就是一种包裹在文化中的哲学景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这里,哲学的含义就是美学的含义,“万物负阴而抱阳”,它所彰显的就是一座城的仪态,即在一种谐和、恬静、安详的氛围中,民歌的给养一直是丰沛的。在旬阳,道释儒三种文化交融荟萃,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民歌,这样的影响犹如深潭中的潜流,它的张力虽是隐性的,但具有时间上的持久性。侯红艳懂得民歌的丰厚内蕴取决于对地域文化的消化和吸收,这当然是一种自觉,而这种自觉是民歌永葆生命活力的关键所在。
庄子关于天籁的阐释,是纯自然化的,没有社会的介入、情感的介入,它只是自然生态环境原始状貌的一种反映。著名美学家叶朗说:“美是人与世界的沟通和契合,是由情景相融、物我同一而产生的意象世界,而这个意象世界又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真实的显现。”这就再次肯定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也即是侯红艳书中所述民歌之美的要义所在。脱离自然生态环境或脱离文化生态环境的民歌是不存在的,民歌的天籁之韵诞生于凡俗世界,它所呈现的美亦是凡俗世界的美,是充满烟火气息的美。侯红艳发现并找到了这种美的源头活水,而顺着这条涓涓清流,她还会追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