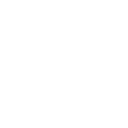涅槃的老屋
刘丰歌
四
院坝下面的竹林还在,但只剩下稀稀拉拉的一些了,如瘌痢头上的毛发,上面覆着积雪。似乎主人搬走,它也孤寂落寞,无精打采地垂着头,早没了当年的生气。三哥说有年竹子开花,许多竹子死了,只剩下这些竹子还坚强地活着。在我的印象中,以前那竹园可是十分茂密的。春季长出的嫩嫩竹笋,曾改善我满嘴萝卜白菜的味蕾。而一条蛇,曾让我对竹林心生恐惧和敬畏。我本以胜劵在握的姿态端着竹竿向盘据在竹枝丫上的一条菜花蛇发起攻击,谁知那蛇对我这小屁孩的下三滥手段根本不屑一顾,昂起它高傲的头,迎着竹竿头上那熊熊燃烧的稻草一个弹跳,便紧紧缠上竹竿,动作潇洒如体操运动员,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手握的方向梭来。我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以人类特有的智商迅速扔下竹竿撒丫子便逃。人蛇的那场较量最终以我的惨败收场。从此好长时间心有余悸。以后春、夏、秋三季再到竹园去玩必先观察竹子,看上面有没有蛇。
那郁郁葱葱的竹园中有多少根竹子经篾匠师傅的巧手编织,变成了我家的背篓、挎篮、筛子、簸箕、晒席。当然父亲也把这些东西拿到镇上卖成钱,换来煤油、食盐,家人的衣服鞋袜,母亲的针头线脑,还有我的钢笔、墨水、作业本。这一园竹子,是让全家最值得骄傲的经济作物。父亲对这块竹园便另眼相看,呵护有加,经常拿弯刀砍除竹园中的荊棘杂草,不让竹子受半点委屈。那竹子也恃宠而骄,不断蚕食旁边的庄稼地,面积越来越大。父亲宁可少种庄稼也舍不得砍,竹园便越发招摇显摆了,同时也以其四季常青的色彩成为老屋一道靓丽的风景。
五
竹园中有几株阳雀花树,春天开出一树黄色的花朵,十分娇艳美丽。我因它美丽的花朵而变得热爱劳动,暂时把母亲赐给我的“懒惰”这个词一脚踹了出去。背着小竹篓摘满一竹篓的花回去骄傲地向母亲邀功,得到的奖赏就是阳雀花炒鸡蛋的清香。其实这才是催生我干活的真正动力。如今,阳雀花树也不在了,阳雀花炒鸡蛋的香味也消失了。消失了的还有竹园中那根大核桃树。那核桃树有一人合抱那么粗,半边已经朽烂,树也佝偻着,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仍坚强地活着。可能是越老越爱自己的孩子吧,那核桃树结的核桃壳厚且核桃仁在壳里藏得很深,卡得很紧,感情特深似的,很难完整剥离出来。这种卡壳核桃吃起来特别费劲,得拿根竹签将核桃仁往出挑,一个核桃要吃得干净不浪费那是不容易的。每年核桃外面青皮开口,露出褐色的硬壳时,我们便用竹竿打下来,捡回去掉青皮,太阳下晒干或放在竹筛中挂在火塘上烘干,除当时零星吃一些,父亲会把核桃用一个布袋装起来,放在他那专用的木柜中,再上一把锁,只有等到过年才把核桃拿出来再让我们吃。常幻想悄悄拿来父亲的钥匙打开柜门取几个核桃解馋,但有贼心却没贼胆,脾气暴躁的父亲那动辄扬起的巴掌可不是好惹的,最终只能幻想一下而已。听三哥说后来核桃树老死了,被砍下烧了火,做了饭。这核桃树将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了我们家,是值得树碑立传的。
和核桃树一同消失的还有老屋门前菜地里的一株大柿子树。那柿子树约有二十多米高,身板挺得笔直笔直的,颇有绅士风度,斜出的枝丫大都靠近顶端,结的柿子个很大,形似磨盘,我们叫磨盘柿。下面却是光溜溜的一截躯干,可能不想让人轻易采摘它的果实吧。每年柿树挂果时,满树小柿子会掉下许多。我小时喜欢捡来用竹签从柿蒂处插进去,用拇指和食指使劲将竹签一搓,立马将小柿子放到桌子上,那小柿子便能旋转很久,这是我小时的玩具之一。自己动手发明,快乐尽在其中。待柿子长大成形时,还是青皮的,特别苦涩,是不能吃的。但这难不倒聪明且好吃的祖先,他们早就发明了泡柿子的做法。我们只需如法炮制,将青皮柿子摘下来,然后再采些蓼草,和柿子一块放进大锅中,将清水倒进锅,淹没过柿子,然后盖上锅盖。剩下的事交给蓼草和水吧!不知蓼草使了什么魔法,能在水的帮助下将青柿子脱胎换骨,只需一个礼拜左右,就将涩涩的青柿子变成脆甜可口的泡柿子了。若柿子泡好,揭开锅盖,能闻到一股甜丝丝的气息,还能看到水中不停地冒着气泡。细听,还有“嗞嗞嗞嗞”的声音,可能是蓼草在对柿子传经布道吧!这时泡柿子就成了我们的零食,每天上学前都要揭开锅盖拿几个装在衣服兜中,到学校和要好的同学分享。有时父母亲也将泡柿子背到镇上去卖,二分钱一个,买的人还很多。待树上的柿子变黄时,又有了另外一种吃法,将柿子摘下来,刨去皮用绳子串起来挂在房檐下,经风吹日晒,冬季到来,上面结上一层白霜后就变成柿饼,可以吃了。保存到春节,也是招待客人的一道零食。秋冬季节,树上剩下的柿子一个个陆续熟透,变得红红的,像挂了满树的灯笼。其实这是柿子树专门给鸟们留的食物,它是有博爱心肠的树,绝不因人类高高在上便巴结逢迎。这时,鸟儿们便成群结队到树丫上享受天赐的美食。一群喜鹊在树顶枝丫上垒起了两个窝,且一住就是好多年,从不搬家。一些熟透的柿子东一个西一个掉下来,摔烂在地里,有的碰巧摔到树下的杂草中,保留比较完整,我们碰到,便会捡起来用嘴去吸里面变得甜甜的汁液。那柿子树虽属我们家,我们家却没人能降服得了它,因为树太高,要摘树上的柿子必须要爬上树去用长竹竿做的夹竿才能采摘到。我们家没一个爬树的能手,每年采摘柿子,只能请我那叫福哥的堂哥帮忙。堂哥人精瘦,却是远近闻名的爬树高手。他摘柿子前将一根长绳一头拴在腰间,一头扔在地上,脱掉鞋子,仰头瞅瞅树身,考察好攀爬的位置,在双手掌心“呸呸”吐两口唾沫,再双掌合十搓几下,身子一跃,就像猿猴一般四肢紧紧贴到了树上,然后借助双腿和胳膊的力量,身子在一伸一屈的自由转换中,很快就能攀到柿子挂果最多的地方,先将自己选个结实的枝丫站好,再将系在腰上的绳子在粗树干上绕一圈捆紧打结,防止万一不小心掉下来有绳子拴着。最后再用绳子将夹竿和背篓吊上去,将背篓继续用绳子吊住,用夹竿将柿子夹下来放进背篓,采满一背篓再将背篓用绳子放下来。后来,福哥在外打工因工伤去世,我们家就再也吃不到他采摘的柿子了。如今那粗大的柿树也被三哥砍掉拉回家准备做家具用了。福哥和柿子树,都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连载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