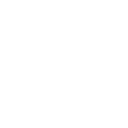西方现代生态文学萌发的根源
杜光辉
文学创作的题材非常广泛,我把生态文学单列出来,因为这是一个足以毁灭人类的灾难性话题,必须引起全社会和作家们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总和,同时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也是人类历史对大自然破坏的总和。
世界自然基金会2006年10月25日公布的《200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地球。1960年代人类每年消耗地球再生能力的60%;如今已经上升到120%,地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00%,人类每年消耗的资源需要两个地球供应才行。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人类危机的报告《成长的界限》,指出如不有效抑制经济与人口增长,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在100年内毁灭。
中国学者鲁枢元认为:“如此下去,毁灭的只能是因环境破败而难以存活的人类,没有了人类的地球反倒会迎来生态的第二度春天。”
2000年,英国学者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
《灭绝——进化与人类的终结》的作者迈克尔·博尔特,绝望地叹息道:“事情的变化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控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使自己停下来。”
人类在使用独木舟、人工织网捕鱼的年代,对鱼类的索取由于技术原因被限制在一定程度,不可能超过鱼类的再生能力。有了远洋巨轮,可以在地球任何水域捕捞鱼类,远远超过了鱼类的再生能力,使许多鱼类濒临灭绝。人类用铁镐挖矿,用土炉炼铁的时代,对铁矿资源的破坏因为技术原因,被遏制在一定范围内。没有汽车的年代,人类修建的桥梁满足车马行人通过即可,有了汽车,桥梁的承载量必须大大增加,从承重10吨的桥梁,到20吨,到50吨,人类竟制造出载重100吨的汽车。天哪,载重100吨的汽车连底盘的重量是多少?如果人类制造出载重1000吨的汽车,又需要修建承重多少的桥梁?
今天的人类,衡量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否,主要指标是向大自然索取资源的能力。从独木舟到远洋巨轮的捕鱼、从铁镐挖矿到定向爆破,从农家肥料到化肥使用,从骑驴跋涉到机动车辆,从骑马传信到互联网信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的掠夺已经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地下、远海、高空、沙漠、森林、高山、陆地、空气、无一能逃脱人类的“魔爪”。
地球生态的危机,早在18世纪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焦虑。那时期的中国,还处在大清王朝的道光年代,没有出现大工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生态仍然处于平和境况。
当时的欧洲由于蒸汽机技术的成熟,开始进入大工业时代,加剧了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同时萌发了现代生态文学。
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28岁的梭罗独自来到瓦尔登湖畔,建了一间小木屋住下。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写出了《瓦尔登湖》。这本书描写了瓦尔登湖的月光水色,晨辉夕阳,碧绿植物,本人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简朴生活,内容丰厚,意义深远,像个智慧老人闪现着哲理灵光,又有高山流水般的境界,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澄明、恬美、素雅的世界。
加拿大著名生态作家法利·莫厄特,其著名长篇纪实作品《鹿之民》。描写了一个即将消亡的北美因纽特人部落的悲惨状况。他们靠狩猎驯鹿为生,商品的介入给他们带来致命的打击,资本家为了攫取高额利润,给他们提供武器,倒在枪口下的驯鹿堆成了小山。由于大批驯鹿被屠杀,没驯鹿可打了,2000人的部落饿死到只剩40人。他们为减少食物消耗,许多人从窝棚里走出,让严寒结束自己的生命,通过自我消灭的方式,与所剩不多的驯鹿达成新的生态平衡。
还有更早的《西雅图》宣言,印第安人生存的美洲大陆有广袤的草原、湖泊、森林、野兽,他们过着只取所需却不贪心的生活。白人在1854年提出以15万美元强迫购买各部落的土地,西雅图酋长发表了一段令人感动的演说,呼求人与人,人与土地应该和谐共存,提出“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我们的一部分。”的生态观点。
研究现代生态文学的学者认为,现代生态文学除了《瓦尔登湖》《鹿之民》之外,还有8部作品,分别是:
《弗兰肯斯坦》(1818)的作者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创作的小说,是第一部反思和批判科技过速发展的作品。它预言人类以科技发明主宰自然,反过来被自己创造的科技所主宰,预言与自然为敌的科技发展必然导致生存危机。
《沙乡年鉴》(1949)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作者创建了大地伦理学,主张从生态整体利益的高度,衡量每一种影响生态系统的思想、行为和发展策略。
《天根》(1956)的作者是法国作家罗曼·加里,这部小说提出,保护生态必须与维护贫困民众的生存权利相结合;国际上的生态不公正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破坏生态的理由。
《寂静的春天》(1962)的作者是美国作家、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作品揭示了滥用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抨击了依靠科学技术来征服自然的生活、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
《沙漠独居者》(1968)的作者是美国生态作家爱德华·艾比。艾比提出唯发展主义推动现代文明从糟糕走向更糟糕,导致“过度发展的危机”,最终使人类成为“过度发展”的牺牲品。
《有意破坏帮》(1975)的作者还是爱德华·艾比。小说描述了通往新修建拦水大坝的大桥通车仪式上,大桥被拦腰炸毁。试图通过类似工业革命时代,捣毁机器的破坏性方式,阻止人类对地球生态的破坏。
《死刑台》(1986)的作者是俄罗斯作家艾特玛托夫。小说通过对人与狼的关系的描写,揭示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荒谬,批判了人类毫无生态伦理的暴行,提醒人们应摆正自己在自然万物中的位置,打消虚妄的高傲,唯有这样,人与万物才能重建和谐关系。
《“羚羊”和“秧鸡”》(2003)的作者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讲述的是发生于20世纪的科技癌细胞突然扩散,人类在贪欲和妄想的驱动下,使科技畸形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从18世纪起就有了现代生态文学的萌芽,这些作品对人类挖掘并批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确立生态意识、构建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应该认为,现代生态文学源于西方。
(连载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