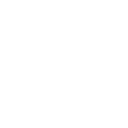那年中考
□ 卢慧君
又逢高考季。考场外,乌泱泱候考的家长,在烈日下汗流浃背,满脸的焦虑,即使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无法喘息的沉闷、紧张。
没参加过高考,但我的中考之路艰难曲折丝毫不亚于现在的高考。上世纪八十年代,考上中专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一旦考上,一个编制内的工作就有了着落。学生首先要通过考试取得资格,名额由地区教育局分到各市县,由市县分到区公所,最后由区公所文教办根据学校规模和上学年考取中考情况分配。本来名额不多,层层扣留一点,到了学校也就不多了,通常一个学校两三百个毕业生就十来个名额。那时农村条件差,没有人进城上学,所以农村生源还是不错,一个乡镇一所初级中学。只记得那时,一些学校两三百考生,没一个考上中专的。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考中专是“鲤鱼跳龙门”改变命运向上流通的最佳选择,因为原安康市没有规定复读生不能再考,导致大量的落榜生选择了复读,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要么考上,要么自认无望自动放弃。汉滨的考生,应届生基本无望,至少我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考成功的。
虽然我的成绩在应届生里名列前茅,因为前面有复读了两三年的学生,我就没有优势了。选拔赛下来,我既盼着结果早点出来,又害怕结果出来,那种等待分分秒秒都是一种煎熬折磨。结果出来后,我的名次很尴尬,排在12,名额10个。老师后来讲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只悔恨自己没有多考一点点,回家怎么对父母开口?家里对我抱着很大的期望,我害怕看见父母失望的眼神。那几天,我天天迟到早退,无心学习,一个人在田野里游荡。然后就是陆续有同学家人花钱找关系弄到了名额。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去找谁?据说一个名额一百块,那也不是小数目。我什么都没对家人讲,失落、懊恼、羡慕……所有的一切都一个人默默承受。学校领导也是天天跑,想尽量多争取几个名额,最后,临考前的十多天,我才获得了那个极为珍贵的考试资格。
因为太想考上,导致考前连续两晚整夜失眠,陷入越着急越无法入睡,越无法入睡越着急的恶性循环中。我知道,这种状态绝对没戏。第二天昏昏沉沉走进考场,早上语文我已记不清,但下午的数学还有印象,一道12分的函数应用题,稀里糊涂中做错了。下来和同学对答案,知道是课本上原封不动的例题时,那个懊恼无以言表。因为太疲惫,我居然在英语考场上我睡着了。
复读是必然的。这时,我对自己是信心十足,如果命运不捉弄我,应该没问题。我的各科成绩都不错,特别是数学,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曾经过层层选拔,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国“奥数”竞赛,作文和英语也不错,多次竞赛中获奖。这次的资格试,我没有任何悬念地拿到了准考证。
考点在培新小学,我们头天早上从学校统一乘车。一直好好的,临出发前,我毫无征兆地上吐下泻,想在药店买药都来不及了。父亲见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怕就是这个命。”父亲那种失落、痛心的神情我现在都记得。我也是一阵揪心,既对自己,也对家人。我怕错过出发时间,连感叹和伤悲都来不及就匆匆走了。
还好,那阵过后没有出现过什么不适。答题很顺利,即使窗外刺耳的电锯声,也没有影响到我。当我拿到意料中的录取通知书时,最开心的是我的父母,做事不愿张扬的父亲,破例请客办了酒席。
三十年倏尔远去,但关于中考的很多细节却是刻骨铭心,人生大半已过,我并没因为跳出“龙门”让我的人生绽放出多么靓丽的光彩,甚至不如那些没有考上在外的打工同学。他们凭着一份勤劳,把握了机遇,在北上广一线城市站稳了脚,而我依然在家乡为生计认认真真地做一份平凡的工作,把诗和远方藏于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