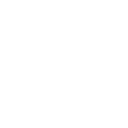灯

郭华丽
小时候每年的团年饭后到天黑之前,我小小的心绪都会处于一种现在可以称之为“幽微”的情态之中。因为这段时间我未出阁的姨姨,舅舅,舅家的孩子以及我左邻右舍的玩伴都去给黄土之内的老先人上坟送亮了,而在我们村我们没有一座可供我们上坟送亮的祖坟。现在想起,我还能记得我当时“幽微”的情绪里是隐含有羡慕的。这“羡慕”里有对人家一大家人同去一处目标一致的热热闹闹,又有一种根之所系认祖归宗的归属感。我不知道我的两个姐姐是不是有着和我一样的心情,但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就会知觉我们和村里其他孩子其他家庭的不同。“回你们山外去!”这样的话语我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听过,也不止一个村人或真或假,或嗔或怒扔给我。“嫁出门的女子泼出门的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的封建残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被村人化繁为简为对物质利益的保护。我们这个外来户安家在了村上,就得从组上领取母亲一年到头劳作的工分所换取的不多的粮食;就得耕种村里的土地;就得分吃村里夏季时时干涸的两眼泉水。母亲嫁给了父亲,依照常理,母亲应当住在自己的婆家。但从咸阳农机学校毕业自愿要求支援山区建设被安排在旬阳工作的父亲,终得在旬阳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家。成为村里的外来户是母亲的命运使然,却是父亲理想誓言的落地生根。在信息、交通闭塞的七八十年代,村人眼里的“山外”与“山里”隔着的是一座望不见尽头的秦岭。在父亲母亲心里关中到陕南这八百余里的地下已根系相连,两盏血脉亲情的长明灯映照八百余里归乡路。
2005年农历4月30日晚上11点多,我看见父亲身子斜倚在我卧室的门框上,探头看着我和孩子说:哦,我娃睡了。猛然就听见楼下传来母亲的嚎哭。还没从自己的梦里完全清醒我就跑到楼下,而父亲已经永远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历经三年眼见病魔把一个自持、自尊活生生的人摧残的双目失明不认识自己,不记得亲人,只剩一具苟延残喘的躯体。死亡对于我们已不可回避,是以天记,以小时记,甚或只是下一分钟。“人生不觉六十年,往事历历在眼前。自知识少游书海,自感平凡学前贤。生老病死寻常事,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是父亲离世前一年口述让我帮他记下的诗。死亡,对于父亲也许从来都不是一件让自己恐惧的事。父亲被安埋在了我们村上。2005年对于我们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和父亲永别;这一年父亲这颗大树永远根植于这方土地;这一年我们在年三十的团年饭后也有了一棺可以去祭拜送亮的坟茔;也许从这一年起我们才真正把外来户这个称谓彻底丢掉。
记得父亲离世时我几乎没有失声痛哭。生了三个女孩的父母没有要那个女儿顶门立户,最小的我一直和父母亲住在一起。父亲离世,整个事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亲人吊孝下跪我得跟着一次次跪下,遗体告别仪式上的一切礼数我们都得悉心做好。我来不及悲痛,也不知道悲痛给谁。我用我所有的一切理性来支撑我无望、混沌的心智。父亲这盏灯熄灭了,我们必须守护好母亲这盏微弱的生命之灯,这盏灯不仅要照着母亲走完她的余生,也将照亮我们一家人前行。
在我们通往楼顶的檐下挂着一盏花灯。2004年的春节我们村里计划玩社火,大舅娘年前就跟我母亲说要在社火玩结束时帮我家偷一盏花灯。我听外婆说过,若是谁家连年时运不济,在过年玩社火时会让相知相亲的人帮忙偷一盏花灯挂在家里冲喜,这个家从此就可摆脱霉运,走向顺遂。从2003年父亲发病起一年比一年病情加重,舅舅、舅娘眼看父亲被疾病折磨,母亲整日守在医院,我们医院单位家里几头跑,家不像个家的样子,就期望用偷花灯冲喜这种方式能让父亲好起来,冲走我家的“霉运”。对于舅娘的心意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荒诞,对现实的心力交瘁让我们寄希望于冥冥中的神,天可怜见,神若不忍?
这盏灯是舅娘用一个红绸缎面包着在正月十六的夜里送到我家的。这盏有着四个缀花吊坠的花灯从偷来的那夜就一直挂在去往房顶的檐下,父亲不在了,它还在。十几年里我们谁都没动它,任它落满岁月的风尘,在时光里失却了本色。我一直回避它的存在,怕它落在我的眼睛里就揪起我的心疼。不小心看见它时我就会想,如果它是有知觉的,有一双眼睛,这么些年它都看见了些什么?去年腊月23除尘时我把这盏灯取下放在炉火里烧了,它其实只是一个道具,它看不见人间悲喜,负载不起人世愿心,发不出救赎的光。继续的生活承载不了太多哀痛的记忆,我让我的某些记忆和它一起化为灰烬。我们活着就把父亲的那盏灯点亮在我们心里,我们得自己端起灯照亮自己前行的路。
2005年的团年饭我们吃的比往年早了些。从今年起我们需要在天黑前给黄土之内的父亲上坟送亮。从今年起我们的团年饭已不是团圆,父亲在地下我们生活在人世。倏忽之间就是15年,悲痛一年一年被稀释,母亲一年一年老去,母亲的这盏灯亮着,我们的亲情都有归处。
小时候,父亲也曾在年里给我做过一盏灯,是一盏竹篾编制有四个小木轮的兔子灯。父亲在糊灯的皮纸上画上一株待放的墨梅,又写上了《卜算子·咏梅》这首词。那时的我还不懂得这首词的意蕴,晚上牵着这盏灯出去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总觉得自己的这盏灯同他们的元宝灯、蝴蝶灯、竹马灯有着不同。在这些曾嘲笑父亲不会背背笼的伙伴面前,我藏在心里的优越感被我紧闭的嘴唇安耐住:我的爸爸会画画,会写毛笔字,会识谱,会唱歌,你的父亲会么?!父亲躺在地下已经十五年了,若说死亡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存在,不知道父亲会不会因为自己坟前的变化也感知得到生活、时代的变化?从2005年一块方木板,一根竹篾,一张长方形红纸糊成的灯笼到折叠的纸灯到现在的电子灯。从一小挂芝麻编到一团大地红到现在直冲天宇五彩缤纷的礼花。父亲收到的不仅是我们的祭拜、惦念,亦能看见我们物质的富足、心灵的安适。
父亲活着时也曾数次带我们回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如今我们给父亲上坟时,会给父亲叮咛,让父亲带一些钱分给老家黄土内的爷爷奶奶,多送的两盏灯是给爷爷奶奶的,也要父亲一定送到。还是有期望:爷爷奶奶与父亲已同在一个世界了,华州区与旬阳这三百余公里的距离对于爷爷、奶奶、父亲已不再是地域意义上的距离了;我们在为父亲点燃一盏灯的同时,老家的活着或死去的亲人也同时为远离故土的我们和黄土之内的父亲点上了一盏回家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