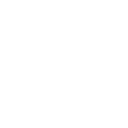爸,您还是种地吧
殷金来
我弯着腰,扶着蹒跚的父亲。一边指着正对门的土地说:“爸,这一季的庄稼大多都背了两个砣呢。”又指着一块已经青黄的麦地说:“今年的雨水格外听话,麦子比去年能增收一些。”
那时父亲需要我搀扶着,才能吃力地挪开有些抬不起的腿脚。父亲已经需要借助外部的支撑才能勉强维持在这个世界多站上那么一会儿。但是父亲看着自己种下的这一季庄稼枝繁叶茂即将丰收的景象,身体里就像灌注了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让他有些弯曲的身子挺直了很多。或许这是父亲种在土地里的最后一季庄稼了。父亲也像快要倒伏的老熟的麦子,根部和躯干的营养水分都供给了上面的麦粒,离地面越来越近。但我依然感觉到了父亲身体里透出来的那种想站着的欲望。
生命都会被大地收割,我扶着父亲一步一步细细地看着这些充满人间情谊的土地,这些沾满人间烟火的庄稼。我只是想让父亲的老熟期尽量能够向后推迟一点,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再留下一季春播秋收的希望,自私地想从父亲这一蔸庄稼里再获得一些温暖。
母亲的离去,加速了父亲的衰老。我看着父亲一日一日萎靡下去,心里暗暗焦急。我想给父亲换一个新的环境,父亲明白我的想法,但他依然遵守着内心的坚持。我知道像父亲这种内心有着坚持的人,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其实父亲在我眼里并没有很多事情需要花费时间。他留守在老家,只为了半亩菜园子,十几只鸡,几分烟地和靠老天爷吃饭的承包地。而这些完全可以搁置下来。面对父亲的坚持,我只能默默保留我的意见,同时口头支持他的决定。因为我没有更好的借口来说服固执的父亲和我一起离开。
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我原以为精神状态会一日一日消沉下去的父亲,竟然迅速地从萎靡不振中恢复了过来。像一棵眼看着枯黄的老树,又充满了树青叶绿的旺盛。父亲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那次回家,父亲把门上了锁。我知道父亲去了菜地,顺着门前的村道找到了对门坡上那块自留地。那块自留地被父亲养得很肥,玉米、黄豆、荞麦、天星米构成不同的图案组合出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父亲精神很足,面色红润地湮没在庄稼里。我看见父亲把萝卜和红薯堆在一起,就拿了背篓往进装。父亲高兴地说,不用那么费力,叫亮儿用三轮车来拉。父亲还说剪茶不需要剪子了,有了修剪机。父亲越说越兴奋,亲手端着修剪机,做起了示范。看着父亲,我突然明白,土地对于父亲,就是父亲一生能够自由徜徉的水域。父亲在土地里,能够获得滋润生命的力量,让枯败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如果把他赶到城镇,就像把一株玉米从土地里拨了出来,父亲肯定感到慌乱和无所适从,虽然在阳光舒适的环境下,但很快会流失水分从而早早地枯败下来。
父亲忙了一会,闲下来给我讲科学种地的效益,以及订单农业的好处。接下来他又满脸红光地跟我算账,种一亩茶和种一亩玉米的投入产出和效益比。父亲说到高兴处说:“明年我去把学校那块集体土地承包下来,种一块燕麦。”我被父亲的雄心壮志惊呆了,年过七十的父亲种这么宽的土地,难道还要像年轻时一样挥锄舞铲,大种四方!
我还是压抑着惊异,显得平静,学生一样虚心点头。论种地的功夫,父亲的确是这一行业里的专家。但是种地是需要体力的,父亲从哪儿来的体力?这种事情大概说说就算了,可父亲明显来真的了,积肥储种,闹得不亦乐乎。只要我一回到家,不管我愿不愿意,父亲便指挥着我不是整地就是储备粪水薅草施肥。我又不能打消父亲的积极性,只有咬牙坚持或者悄悄请劳力。这还不能明说,还得遮遮掩掩说是附近的邻居甘愿帮着。只要父亲高兴,出这点钱在农忙季节请几个伙计就是小事。
父亲心里高兴,我的心就轻松下来。我一直担心母亲离去后,父亲的心里有放不下的包袱。看他这样开心的样子,我也跟着开心起来。尽管玉米不值钱,往往投入的费用比收回还有些欠缺,而且收得多了被父亲当作宝贝一样送来拥挤地堆在一起,已经成为了我要随时处理的负担。但为了让父亲觉得劳有所值,父亲问起肥料的价格,我常常把几年以前的价格说给父亲。只要父亲开心,我就是花费一些钱,多买一些肥料,多请几个帮工,我都心甘情愿。我给父亲提供种子和肥料,再经过父亲的手进行回收,这个过程不仅满足了父亲种地的心愿,也让他有了满满的获得感。就是浪费了肥料和精力没有收成,只要父亲开心地耕种着土地,就能够从土地里获得安慰。
我没有回家的时候,父亲会忍不住隔上几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还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今年的莲藕又面又嫩,屋檐的挑上挂满了金黄的玉米。父亲还说,公路硬化到了门口,走人家特别的方便。我也为村子的变化感到高兴,不仅是公路,还有吃水,医疗都大大得到了改善。于是我决定不打乱父亲的节奏,那是父亲早已适应了故乡的节奏,那是在土地里长时间劳动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定式的节奏。
父亲种地在身体里种出了精神,显然有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父亲不主动提起,我也不会过问。问得太多,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同时我不再向父亲提出跟我居住的想法。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注意到父亲说话的语气有点异常。每次父亲和我说起庄稼的事,都会小心翼翼地分析我的话外之音,仔细回味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而且每次和我说话,也似乎越来越有拒绝我的底气。他的神情似乎在说,看我还能种出庄稼,而且村子里的条件现在都这么好了,有看病的地方,有买东西的地方,要忙就忙自己的去吧!可我又分明能听到他心虚的犹疑。
我要给父亲一个更足的理由作借口,让他一心一意地打理着几亩地的庄稼。父亲只有种上庄稼了,才有精神,沾着泥土就会像庄稼一样旺盛葱茏。父亲种不了土地了,就会迅速地枯黄,再不能像树一样撑住站立的腰身。我对父亲说,种出来的粮食,自己吃不完,我放到街上去卖,有好多人都在打听有没有本地农产品销售呢,紧俏得很。我说:“你愿意种地,只要力气能吃消土块,差什么我都托人去批发回来。今年秋天了,再把房子修一修。”
那天帮着父亲做完活,已是晚风习习。父亲坐在土埂上,吧嗒着烟锅。父亲喊我坐下,吸了一袋烟锅后,几次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我有些奇怪地望着父亲,但是我又有些懂了父亲。父亲沉默地看着土地,似乎和土地在做着一次对话。父亲在夕阳西下的暮色里,坐在土埂上,没有说话,只是望着面前那块和亲人一样的土地,在用眼神无声的交流。他的表情有些沉湎,痴迷,好像沉浸于某个世界。
我对使劲吧嗒着烟锅的父亲说:“爸,您还是种地吧!”
在父亲的心里种下一些庄稼,他的内心装满了土地上的一切,才没有打着马虎眼抽身离开土地的机会。而那把无情的锋利的镰在伸向父亲时,在时光里才会有一刻延时的停顿。
如今,父亲离开我已经快十年,可我每次路过父亲种过的土地,依然还会看到父亲在土地里劳作的影子,我知道那是父亲在我心里永远的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