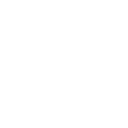涅槃的老屋
刘丰歌
九
现在我就站在老屋原先堂屋的位置,那里原先摆了一张农村常见的“八仙桌”。桌子四周各放有四条长凳。平时这些桌凳只是摆设,上面放些杂物,只有逢年过节或父母亲过生日招待贵客,才用这张桌子吃饭的。靠里墙的位置摆放着一个石磨,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玉米磨成玉米糁子和玉米粉,逢年过节也用它磨豆腐。堂屋的阁楼上就是我家的粮仓,收获的稻子、小麦、大豆、玉米都储藏在阁楼上。堂屋地下还挖有一个地窖,地窖里专放红薯种子,有时里面也放些过冬的土豆。堂屋一个角落,还用竹篱笆隔出一个小房间,里面支了一张床,类似一个客房,家中如有客人来,一般安排在那个房间休息。
向东跨过四五步,就是灶房了,灶房是母亲的领地,她在这间房中用普通的食材为我们做出普通却可口的饭菜。房中有火塘,有大灶。火塘做饭,烧水,烤火取暖,熏制腊肉。大灶三锅并列,从小到大,像一母所生的兄弟。小者炒菜,中者炒茶、做豆腐,大者平时煮猪食。碗柜立于灶旁木架上,灶背后立着罐架,放着几只大小不等的吊罐。一字排着的还有一个大案板,案板上放着每天必用的锅碗瓢盆,案板架子下放着几个腌泡菜的坛子,坛子腌着酸萝卜、酸豆角、酸辣椒。一年四季可吃。每当揭开盖子,一股泡菜的酸味便会直冲鼻孔,是酸得人直流口水、却又想吃的那种味道。火塘旁还摆放了一张小方桌,是平时家人吃饭的地方。灶房是母亲的舞台,母亲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了一生,操劳了一生,直到她生命的灯盏熬干最后一滴灯油,她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才画上了永远的休止符。
向西跨六七步就是两间卧室,我们陕南人叫歇房的地方了。歇房是七十年代初才盖的,原来只有两间房,一间当灶房,一间当歇房。几个哥和姐长大后房子实在不够住,父亲便接着又盖了两间歇房,歇房中间还是用竹笆篱隔开,阁楼上再支床,这样保证了每人睡觉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歇房在我的印象中是既怕又爱的地方。儿时胆特小,每次我瞌睡来时,大人们还在忙着其它的事,只能我自己先到歇房睡觉。我睡觉时自己是不吹灯的,害怕黑暗中藏着妖魔鬼怪。但为了节约煤油,亮着的灯常被母亲进来吹灭或端走。这时我的内心便恐惧起来,头便本能地钻进被窝,用被子把自己蒙严,在惊恐中慢慢入睡。后来我家养了一只小花猫,那猫就成了我最好的伴,每天睡觉非要把小花猫抱着和我一块入睡,但小花猫的生物钟很难和我同频共振,就常在被窝中反抗,用头使劲擂被子往出逃。我却不理,硬把它捂在被子中,直到它就范,我睡着。待长大些,不害怕了,也上了学,却感觉永远也睡不够,晚上干完父母亲安排的家务活,做完当天的作业,洗漱后头枕上床很快就能进入梦乡,早上还在睡梦中就被父母亲喊起床,然后洗脸热饭,吃后背着书包上学。除了周末和寒暑假,天天如此。
若周末或放假在家待着,最盼望下雨和落雪。下雨天,大人们也没法干农活,难得能在白天睡个午觉。这时,我也能跟着沾光,躺在床上,听着大人的鼾声和雨水打在瓦片上的“嗒嗒”声,想着自己的心事,便觉温暖惬意,岁月静好,但愿时光停滞了。落雪天,除了能睡懒觉,还有鸟到院中雪地觅食,便可像鲁迅文章中说的那样,用竹筛来抓鸟。抓的鸟儿养在笼中,听它的鸣叫,玩几天再放它回归大自然。更多的是围在火炉边,听家人聊天拉家常,或拿上一本自己喜欢的小人书,一遍一遍地看,直到里面的故事情节烂熟于心,再跑到玩伴家中,把故事情节讲给他们听,炫耀自己知识的丰富。
十
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只能凭我的记忆和想象来还原曾经的过往,不仅感慨如真有时光隧道该多好,我便能穿越到几十年前,重温过去的时光,再听父亲唠叨“做人要懂得感恩”“不能浪费粮食”“要尊老爱幼,扶弱济贫”这些说了多少年的话,再吃一顿母亲做的“紫阳蒸盆子”“酸菜炒蘑芋”“大肉炒粉条”“煎炒老豆腐”等,那该是多幸福的事啊!或者这老屋就是一张大磁盘,老屋被误删除了,压个恢复键,让它再次原还到从前的模样。这样想着,突然发现胸前带的照相机,居然一张相都没照,想起当初探家时带着照相机,给家人照相时总是以门前的竹园和河对岸的山峦为背景,为什么不给老屋照几张照片呢?那时总认为老屋会一直存在着,我什么时候想回来看看就回来看看,它一定会等着我的。可如今,老屋已消失在时间的河流之中。留给我的除了遗憾还是遗憾。
我连忙用相机从不同角度,将这片曾承载我十八年欢笑和泪水,憧憬与梦想的老屋的废墟定格我的相机中。也算遗憾中的一点自我安慰吧!
站在老屋向山下河对岸看过去,公路两旁新增加了许多新建的房屋,大都是两层或三层的小楼,清一色白墙黛瓦。如在城里,这已算很好的别墅了。三哥说都是搞新农村建设,从交通不便的山上搬下来的人修的,原先的房屋大多像我家老屋一样,拆除了。此刻,似乎心有所悟,这老屋多像涅槃的凤凰,它的消失,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浴火重生而已,那一幢幢新建的楼房,不就是新生的老屋吗?既如此,那就让老屋成为心中美好的记忆吧!
原本失落的心也便释然。
(连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