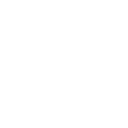让我们多刨出清泉
■ 槐籽
疫情关乎心灵,它促使我们与自己对话,去聆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反问、疑问还是设问,人们都在问自己。在诘问中,剥落掉生活的种种浮华,露出坚硬滚烫的内核。疫情促使人们重新校正人生的航向,或远行,或返乡,我们都选择从“心”出发。文学作为时代的号角,如何面对疫情后社会和心态的微妙变化,该以何种表情示人,特开设“后疫情时代”安康文学的表情专栏,诚邀广大作家发表真知灼见,我们将持续刊发。首期特推出评论家槐籽的《让我们多刨出清泉》,以抛砖引玉。
——编者按
安康文学在新时期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创作者人数、公开发表作品数量、品种齐全程度、在全省全国影响,老中青队伍结构,都是过去时代所不能比拟的。也许你会跟这个判断较真,你会拿出《我来了》《狗又咬起来了》或者崔八娃,来印证逝去的那个时代安康文学的光荣——这没法讨论。因为它不是一个文学理念层面的比较。那个时代的纠纠结结都已然过去了,床铺草再翻它还是床铺草!
改革开放搞活四十余年,安康文学始终伴随着安康经济社会发展全程,安康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同时也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成就。这里主要说文学,所说的“文学”在笔者笔下其实是一个安康文艺的大概念,安康文艺的其它品类与文学一样,与安康的时代发展同成色、同进退。安康文学水平怎样,其它品种其实也错不上下。这样的判断,其实对于安康几十年的文学(文艺)创作者们来说,是很尴尬的,它其实也是说,安康文学四十多年来的发展,依然是后发达的,追赶中的,磕磕绊绊的,甚至言不由衷的,由于是这样的态势,谈论起安康文学的成就,同样也是尴尬的。从“三秦”情况看,陕北、关中、陕南在文学以及在经济发展上的占位进位,甚至未来几十年新发展的进路,都是一目了然的,文学的收获对安康似乎永远都是小年,欠收,从未丰产过。即使与同在陕南的汉中、商洛比,我们也不敢大声喧哗,有一位安康作家私下里说:安康文学落后整整一个时代。
笔者很长时间思考这位作家的这句话。整整一个时代是什么意思?是习惯了跟在别人后头走?是文学的节律与思考老是走在生活与社会的队尾,或者落下很长的距离?是时代进步了,理念更新了,我们的文学还在自足于己,以己昏昏使文学昭昭?我们的创作者们不断提供出来的文学产品,市赢率到底几何?我们作家队伍中,到底有几位总是以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拔高着安康文学的峰巅?以上问句不好深思,也不敢追要具体答案,每每思及,让人一头冷汗。
我们当然不能说在时代飞速发展中,安康的文学缺位了,我们想自责的是,安康文学的在场不能掩盖它的落俗与轻浅。比如在汉江河边的沙滩上刨井,出水再清再多,那也算不得是什么本事。同样在江北的黄土岗上打上来清澈的井水,它就能代表对整个安康地下水丰度的判断,因此你绝对不能用汉江河沙滩里的水量来衡量安康地下水,但事实上,我们或许早已习惯只拿汉江河作证,我们只愿意出示最好的但它并不是普遍的——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也正是这样?很轻易就刨出一汪清泉,然后大声宣布安康从此是鱼米之乡。
文学的深刻决定了文学的丰度。文学时代的深刻,正是一个时代的深刻。物的建设,最终要向质要终极效应,最直接的答案,其实正在文学艺术那里。浅薄的文学追求,或以文学的即时效应为荣满足于文学的新闻报道式表达,最终一定会带坏一个地区的文学生态,它会使这个地方的整个文学之林生病,施放污烟瘴气。因为它普及的一个基本的文学理念是落后于时代发展新理念的,比如文学的功能化问题,比如文学实践的组织化程度问题,比如文学人口的功利心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后疫情时代”,是把过去几十年的问题一次性打破摊在阳光下让大家看: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困扰我们的问题,这就是希望的切口,这就是未来的高度——怎么选择?其实现在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以至个体层面,大家都有思考,都有选择,文学当然也必须作出自己的回答。问题与出路同在,打破与再建同在,困难与希望同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对每个人都是新的命运,文学当此之时,怎样结实地踏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怎样眼光从平凡的人群越过群山,掠过星空——作为先验者的文学,怎样率先找到那一缕给人引路、给人前景的星辉?!
我们的文学,不止于在汉江边上掏出清水,更要在黄土岗上刨出清泉,因为百年变局事实上带来百年改变的机会,就算仅从安康的当下考量,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都面临着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三十年的答题,“后搬迁时代”,乡村振兴,区域引领,生态强市,汉江综合开发,城乡一体化发展,主导产业建设等等,它很具体,很现实,没有标准答案但有标准理论,这也正是安康文学的视野——安康的文学从新出发,从新落笔,从新结果,都必须深刨,没有捷径,没有新花样,“深”和“刨”都是基本功,我们必须在这个百年的大命运中建立起来。这是最后的机会,这个机会错过了,安康文学剩下的就只能是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