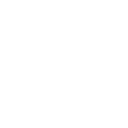想起当兵那些事

□ 李春芳
在四十多年的工作阅历中,岗位变换好几次,单位走了七八个,但很少有人知道我有一段当兵的经历,甚至连子女和亲朋都不知道。直到紫阳县退伍军人事务部上门挂了“光荣之家”牌子后,才有勇气吐露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我不仅是一名退伍军人,还是一个七级伤残军人。
汉江水清澈透明,从巴山深处向着远方流去。1970年冬天,紫阳县政府组织居民和学生敲锣打鼓地把380名新兵送到县城码头,坐上机动木船到安康人武部集合。此时的汉江虽然没有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但常与激流险滩相遇,我们坐在船舱里隐隐感觉到船只经受着风吹浪打的考验。刚穿上军装的新兵们心情如同汉江水一样心潮起伏,既有离开家乡告别亲人的不舍,又有踏上新征程的喜悦。我们到了部队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格外新奇。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到一排二班,领章帽徽一戴,钢枪一背、气宇轩昂、神气十足。在军营里练兵打仗、施工劳动做班务等,我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军事科目样样得优秀,当兵第二年,被评为全团的“五好战士”,在表彰大会上作典型发言。那时部队的军事训练很严格,有时早晨三四点紧急集合,10分钟时间洗漱,背着背包和步枪跑步奔向目的地,部队在几十里地外设置宿营地,吃饭时要求战士们5分钟吃毕,否则就用帽子盛米饭,边跑边吃。部队这个大熔炉把我一个农村青年变成一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自豪的不可言状。至今我仍然保持着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和狼吞虎咽的吃饭习惯,别人一碗蒸面要吃十多分钟,我只要一、两分钟搞定。
2019年“八一”建军节,原所在部队的河南兵,在驻马店举行战友50年联谊会,特别邀请外省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受伤的四位战友参加,我便是其中的一个。那是一个高温天气,中午的太阳毫无遮挡地直晒着中原大地,车站大理石地板热得滚烫滚烫,几位战友夫妇已早早地在驻马店火车站等候着,当我们随人群出站时,战友们就围了上来,昔日血气方刚的解放军战士,如今已变成白发鬓霜的耄耋老人,久别相见即欣慰又伤感,战友们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封存在心里的话儿恨不得一口气全吐出来。在战友联谊会上给我们受伤和立功的战友披红戴花,我还代表来自外省的战友上台讲话。
驻马店是中国古代的皇家驿站,流传着许多驿马硝烟的战争故事。在战友家里,战友们回想当年的部队生活,重述了那些发生在我和战友身上,又不曾知道的一些情节,把战友们的思绪拉回到激情似火的青春岁月。我们团是由北京戊戌部队转为工程兵的,1968年,军委组建161独立团驻扎北戴河。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部队第五天就紧急转移到长江三峡的大后方,宿营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上游的连陀乡,军营驻扎在长江岸边耸立的天柱山下,任务是在天柱山中打通一条隧道公路,为深山里的军事基地服务。我们团三个营全部投入公路和桥梁建设,为赶工期施工实行三班倒,人歇工程不歇。
1972年7月21日,轮到我们排上夜班,凌晨2点一排30多名战士在隧道里紧张地劳动着,一个意外引爆了装有几公斤炸药的爆破装置,当时我只感觉眼前闪烁一道强烈的光束,连响声都没有听到,就不省人事倒下了。没有受伤的战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窝蜂地跑出洞口,等没有动静时才返回施工地,发现五名战士被石渣掩埋,战士们立即刨开土石,从乱石堆里把我们掏出来的时候,个个血肉模糊。我和一名叫张孝堂的战士伤势最重,劳动布的工作服被炸得只剩经线了,胸部以上布满伤口,脸面被鲜血染红。部队用快艇将伤员紧急送往宜昌市军医院进行抢救,到第二天下午4点我做完手术。由于眼部受伤不能用麻药,手术中途我苏醒过来,能听到医生从我身上取出石子置于瓷盘的响声。据医生说,本来要给我那位姓张的战友先做手术,结果他再三推让,对医生说:“先给春芳手术吧,他还是个孩子呀!”当时我17岁,他22岁。做完手术尽管医生不说,但我们也知道,虽然保住性命,却都成了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我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不敢照镜子,常常藏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病友们坐在床边安慰:“坚强些、不要哭,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下战场,这才是好战士”。我一再掩饰内心的伤痛说“没有啊,不是别的,我想爸爸妈妈了!”受伤的战友把我劝住了,他们却哭起来了……
住院期间,我们几个病友同病相怜,相互搀扶、互相安慰,结下生死之交的战友情谊。我的伤情康复得很快,只是右眼视力没有了。可怜我那位姓张的战友,他是1968年的兵,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是连队才子,吹拉弹唱写文章样样能行,提干的文件即将下达,由于伤势过重,加上手术时间延迟造成双目失明,成为一级伤残军人,美好的人生理想、无量的前途事业就这样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经常安慰大家,怕我们想不开,在病房里讲故事说笑话,让我们开心。四个多月后我要出院了,最后一次扶着那位双目失明的战友上厕所,最后一次将病号饭端到他床前。临别时我俩紧握着双手欲哭无泪,我第一次领悟到患难之交的深情厚谊,是一般情况下难以体会到的。他说:“春芳,你先回去,我过一阵就回来,你回连队要好好保护身体,退伍后我们还要找媳妇呢!”在彼此的苦笑中,心里都明白,当兵时我们五官端正、帅气十足,如今已是伤痕累累、面目全非,不说找老婆,就连基本的生活出路都恐难找到,未来生活充满茫然,不知所去所从。后来他先后转院到武汉、上海等地治疗,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好在20年后他儿子长大了,义无反顾地让儿子参军入伍,依然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1973年3月,部队给我了一个伤残军人证,发了24元抚恤金,什么要求都没有,随一批退伍军人默默地回到家乡农村。临别时几位战友买了几瓶啤酒,趁着夜色在营地后面的小树林里偷偷小聚。自那一别就是50年,以后再也没有和战友们联系了。
乡村的五月,正是犁田插秧的时节,布谷鸟在树上“咕咕、咕咕”不停地鸣叫,公社干部到队里催促春耕生产进度,要动员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产,天天统计播种情况和上劳人员,我也不例外,插秧、铲田坎、挑肥、挖地样样都干。在水田里干了十多天后,受伤的眼睛又红又肿,身上还没有取出来石子多处发炎。母亲用艾蒿熬水给我反复冲洗伤口,用蒲公英贴在眼睛周围,边贴边问:“痛吗?”我说:“不要紧,就是头晕”。母亲叹口气说:“娃儿怎么遭受这么大多的罪哟!”
第二年春天,公社书记把我安排到一个民办小学教书,又过了几年让我到公社担任半脱产干部。70年代末,农村信用社招收管理员,我文化考试合格,因眼睛问题而取消录用资格。1980年,国家要从社会招收一批经营管理干部,文化考试我在几百人中的前十名,又是体检不过关没有录用。这些事对触动很大,所以后来不愿意甚至有意隐藏这段当兵经历。
有人幸福快乐,就有人痛苦悲伤,想想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士,什么都想通了。不管怎么痛苦,怎么伤心,日子总是要过的。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拼命地学习文化,参加国家自学考试,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安心当好半脱产干部。1985年,新来的县委书记束光兰知道我了,让我写了几篇命题调查报告后,把我从乡下直接调到县委宣传部任新闻通讯干事,身份仍然是半脱产,后又从县委宣传部调到乡下区公所当区长、书记,户口仍然是农村。
去年,国家成立了退伍军人事务部,退伍军人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政策待遇。我出门坐车坐船乘飞机都减半收费,全国景点可免费旅游,各城市的各类服务部门都设有“军人依法优先”的窗口。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就是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一层人的关怀,宣传祖国的国防事业,展示和平年代军人履行天职的辛劳。虽然,我当兵经历一个既自豪又自卑、既欣慰又沮丧的过程,但无怨无悔。人生道路没有风调雨顺,一切坎坷曲折都是命运的安排,只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一定会有柳暗花明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