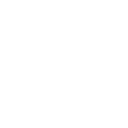从下农村到上三线
□ 余西贵
“天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968年“文革”结束,学生复课,一切开始恢复秩序。当时,我们小学二个年级的学生几乎同时进入了初中,原先小学的同班同学被打乱,由两个年级的同学混合编班。说是复课,其实连书都没有,由于受“文革”的冲击,教师们对学生的教育都是心有余悸而不敢管,上课自由散漫,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作业,像一群散养的羊仔。
我在紫阳一中混了两个礼拜就再也没有去了。后来随家去了农村。
去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生活各方面都十分困难,有时好几天都吃不上蔬菜。农村人一般以家族关系群居的较多,外姓人总会受到排挤的,劳动时总会把一些技巧性的“轻巧活儿”安排给本家人,粗活重活分派给我们这些外来人,至于工分也不可能同工同酬,一般和农村女人的工分差不多,理由是很牵强的“技不如人”。
就这样,我在村上劳动了一年多一点,一次偶然的机会,幸运落在我的头上。襄渝铁路开工,需要在村上抽派民工,村上作为“累赘”把我派去了三线民兵连修铁路。
三线建设也是趣事频发的年代。民兵连有个叫张尔顺的连长,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退伍老兵,解放后回乡劳动,当时回乡也没什么介绍信证明政治身份,组织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他是党员,组织上就登记为党员,后来问他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他说不出来,由于他在刘伯承部队当兵的,就说介绍人刘伯承,弄得登记人员哭笑不得。张尔顺最滑稽的是打电话时对方问他是谁?他说:“我是张尔顺,张尔顺的张,张尔顺的尔,张尔顺的顺。”对方问他在哪儿?他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指着方向:“我在这儿,就在这儿,我一哈儿要去那儿。”还急得脸红脖子粗。
在紫阳境内修襄渝铁路的有个学兵连都是外地来的,学兵连在这里呆久了,都学得牛里牛气吊儿郎当,衣冠也不讲究了。喜欢起哄打群架,冬天穿的棉袄都不扣扣子,用一根绳子在腰上一扎如同山匪,经常三五成群进城闹事起哄,时间长了街上居民叫他们土匪娃子,影响特别不好。
学兵连的女娃子跟男娃都是分开住的,而且分隔距离都较远,女生有封闭较好的厕所,厕所的粪坑露在外面的,有些农村民工娃子天生苕拐苕拐的(蠢坏蠢坏的),当瞅着有女生进厕所时就捡起石块砸进粪坑,厕所内的女生传出一阵骂声。
当时三线建设靠的是人海战术,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铁道兵,有学兵连,也有本地抽调的民工。本地民工村上记工分,另外给我们发生活津贴,比起村上的劳动要优越了许多。
本地民工连队抽派去的人,大都不是村上主要劳力,不是老的就是在村上没特权的人,或是干活比较木讷的人,我在那些人中算是“精英”了。
精英是要受到重用的,连长立马任命我为连队统计员,每天负责统计施工进度。对这份工作我很是认真负责的,由于自己表现极佳,没多久营部抽我去审查各连的财会账务。其中有个连队司务长出了经济问题被撸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营长就让我上任司务长,算是提干了。后来还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正式党员。在那时入党是没有预备期的。
1973年三线建设接近尾声,已不需很多人了,抽派来的本地民工都各自回到村上。由于我在连队的表现优秀,公社书记有意培养,我作为老、中、青三结合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去公社任职。当时正值大专院校招生,我执意要去上学,就谢绝了书记的一番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