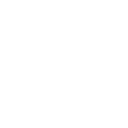我的乡亲,我的父老(非虚构)

张朝林
冬阳灿烂,村道宽阔,两边是林立的高楼,稀稀拉拉的村人,坐在门口,围着一个烤火炉,晒太阳。烤火炉上蹲着烧水壶,壶嘴吐着青烟。二娘也把缝纫机移到院头,踩着踏板,缝纫机“嗡嗡”转,她的门口,挂着花花绿绿裁缝好的衣服。我望二娘,二娘望我,因为二娘对着太阳,刺眼,用手遮住额头才看清,连忙喊:“侄儿子,快上坎上坐,娘给你泡杯茶。”“谢谢二娘,不了,我偷空回老屋看看,顺便在坡上转转。”“折回来在娘这儿坐坐。”
这就是我的乡亲。
二爹是七十年代的铁道工人,二娘是老街上的赤脚医生,街花,也是个出名的“铁姑娘”。她背着药箱,嫁到张家来,成为张家的赤脚医生兼妇联主任。谁家有个头疼脑热,她就上门看病,小孩子半夜发烧,敲她的门,二娘二话不说,背起药箱就走。她还会接生,村子里的娃娃,大多数都是她接到这个世界来的。这些娃娃们,不论辈分高低,都把二娘喊妈,一位按辈分二娘要把人家喊爷的娃娃,不分场合,见了二娘就喊,弄得二娘满脸通红。在抢修阳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70年代,二娘组织全村妇女成立了“斩断梁”突击队,阳安线要从张营村长梁南段通过,必须斩断它。突击队黑明白夜战斗,工地上,人山人海,战旗飘飘,筑夯号子阵阵。晚上,工地上罩着十几盏汽灯,插着火把,亮如白昼,歌声、号子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工地上的宣传广播,不时播放着表扬稿,一个夜里,二娘就上了五次受表扬的广播。斩断梁拿下了,二娘的突击队,挑断扁担28支,推坏人力车轮子25个,用烂的篾篮子不计其数。“铁姑娘”的名字,就是从那个时候喊起来的。二娘没有从医的专业文凭,规范乡村医疗后,她失业了,二爹从工人岗位刚刚退休就走了,二娘把一儿一女拉扯大,女儿在上海工作,儿子在北京工作,都有房有车,接她过去住,她住不惯。巧手二娘,一辈子闲不住,就开起了缝纫铺,爱时髦的年轻人,是不会关顾她的缝纫铺的,她的缝纫,都是为本村和外村的老年人服务的,给赶上好时代的老年人,裁缝红衣绿衣。
走到洞口,恒惠渠的清流从洞口流出,穿过小桥,一股朝张营村流去,另一股泻过陡坡,朝花园流去。
道路两边的小洋楼,形状别致,色彩靓丽,多数门都被“铁将军”把守,往日川流不息的家乡人,都到哪里去了?我的辈分在张营村最低,每次回老家,都要备上好几包好烟,给我的父老乡亲散。每每从村口入,喊哥喊嫂喊爹喊娘喊爷喊婆喊太喊老仙……一路喊来,喊得我嗓子冒烟,一路香烟散过,一摸口袋,几包烟散完了,咋办?赶快在路边的小卖部再买几盒。张营村请客散烟有个规矩,叫硬过一村,不少一户。少给谁散一支烟,那是犯大忌讳的。今天我的这包中华烟,还没有散出去一根。
西边,南北走势的梁叫长梁,东边的梁叫大坡梁,两道高梁夹一个川,夹出了一个五里的小江南,一条常年清澈的小河,从村前流过。往日,田野里熙熙攘攘都是劳作的乡亲,这会儿,看不到人。几条黑狗、黄狗、白狗,田野里晃悠,不时地互相打起来,狗吠声在空旷的村子里窜。
对面走来两位老人,哆哆嗦嗦,挪着碎步。近看,是升子爷和秀婆。升子爷爷认出了我,热情喊我的小名,给我来几句幽默。我连忙掏出烟,给升子爷敬上一支。他连连摆手:“孙娃子啊!升子爷戒了,戒了。”
当年的升子爷,是村子里出了名的“二鬼”啊,怎么就把烟戒了?
“酒还喝吗?”
“也戒了。”升子爷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
“孙娃子啊,想当年你升子爷喝酒,酒德坏,一喝就醉,一醉就打你秀婆,孬种啊!现在想起来,悔死了,对不起你秀婆啊!”这哪是当年火爆脾气的升子爷?
他顿了顿:“孙娃子,你看看时代多好啊,你升子爷还想多活上几年,如果老天爷放债,我还想借五百年哩,好好看看光景哩,这不,罩在脑壳上的二鬼帽子,早都脱贫摘掉了。老来有个伴,才最完美哩。”升子爷脸上漾着笑容。
“哈哈哈”我笑得背过气来,摘掉二鬼帽子,还脱贫哩。
秀婆患了半身不遂,升子爷早早晚晚拉着秀婆在村道上锻炼,真爱感动了上帝,她现在甩掉了拐棍,牵着升子爷的手,可以挪碎步了。
“您年轻时不是不爱我秀婆吗?闹着要换人哩。”我故意逗他。
“年轻时糊涂啊!老烧包啊,老来金不换啊,孙娃子,你看爷,现在多爱你婆不。”说着,他抱着秀婆的脸就啃。秀婆猝不及防,偏着头,另一只手死死抵着升子爷的下巴不放,嘴里嘟囔着:“老不正经的。”脸上却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升子爷的一鬼叫烟鬼,生产队分给他的菜园地,他都种上老旱烟,家里没菜吃,秀婆就提着竹篮子挖野菜。他把孩子们写过的作业本都收起来,卷“喇叭筒”用,用完了,还偷偷撕孩子的课本卷烟。他抽的老旱烟,卷成一拃长的“喇叭筒”,能连抽几筒。一次,他和村中另一个烟鬼打赌抽烟,那位抽到五支“喇叭筒”就醉倒在坡上,他连抽了十支,屁事没有,照样薅草。
二鬼叫酒鬼。张营村有三个酒鬼,升子爷领头。
桂花在村子里开了个代销点,卖散酒。散酒就是食用酒精和自来水在一起勾兑的。桂花卖的散酒,她是把井水烧开,放凉后勾兑的,口感要比自来水勾兑的好。三个酒鬼是桂花家的常客,升子爷酒瘾发了,再忙的活路都丢下,匆匆忙忙赶到桂花家买散酒喝。一次他耕田,酒瘾发了,丢下犁头就走,结果,老牛脱了缰绳,吃掉了人家田里的一块青苗,给人家赔了一斗麦子。
白底黑沿子的搪碗,先打上二两,一口喝下,解个急,然后再打上二两,斜靠在柜台边,慢慢品尝,摇头晃脑。这时,我们看见他品完酒了,就嚷嚷着让他给讲故事,满腹经纶的升子爷,他的肚子里,有掏不完的故事,《三国演义》《封神榜》《隋唐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东游记》等等,他微醉的时候,讲得绘声绘色。我们最爱听他讲《西游记》,他边讲边动作,讲到妖精出场时,扮个妖精脸,张牙舞爪的,向我们扑来,吓得我们后退。讲到孙悟空降妖的时候,顺手拿出桂花家门背靠的棍子,也舞了起来。
一次夏天,半夜时,他酒瘾发了,穿着裤衩子去敲桂花家的门。
“砰砰砰”“砰砰砰”
一次比一次声大,惊得村里的狗咬起来。砸了老半天,门咯吱一声开了,只见桂花的男人,抡起扁担就砍,升子爷猝不及防,肩膀挨了一下,吓得他反身就逃。后来听村里人讲,那次升子爷砸人家桂花家的门,声音大,闪了桂花男人的腰。从此,升子爷半夜酒瘾发,都要忍着,怕挨桂花男人的扁担。
一年冬季,雪很厚,三个酒鬼半夜酒瘾发了,来到了桂花家门前,不敢敲门,三个酒鬼,趴在门缝吸,说吸吸散发出来的酒味,也能过瘾。吸吸吸。不知谁吸的声音大了点,桂花的男人就喊:“外面谁啊?”三个酒鬼吓破胆,悄悄逃了,在桂花家门前不远的小路上跑步。三个酒鬼,冻得成了猴泅,跺着脚,哈着热气,捂着耳朵,不一会,蹑手蹑脚溜到门边,轻轻吸着从门缝里溢出来的酒味。
好不容易熬到东方发白,门还是不开,三个酒鬼是热锅上的蚂蚁,在雪地里转来转去。门开了,桂花扣完最后一颗棉袄钮子,酒鬼们就冲进屋里,先解瘾,再品尝。等到喝上第三个二两,三个酒鬼就天南海北、世界风云地吹起来,都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升子爷就差没说见过美国总统了。
升子爷一醉就打孩子,打秀婆,孩子跑,秀婆躲,他就摔碟子砸碗。这时,谁给他一烧火,他就更疯了。烧火人说:“门槛挖不得,挖了要进雨水。”他偏要拿起镢头,三锤两棒子把门槛敲烂。“柜,可万万砸不得,砸了,装不了粮食了。”他又拿起镢头“砰砰砰”把三格子粮柜砸个稀烂,谷子、麦子、苞谷流得满堂屋。酒醒后,脑壳夹腿下。
那次他喝醉,秀婆没躲过,他把秀婆挑在门前的杏树上,脱光了上衣,用刺条子抽。秀婆刺耳的尖叫声让我们流泪。抽红了眼的升子爷,瞳仁炸开,似乎在滴血,脸上的每一块横肉都在颤抖,咬着呀,切着齿,吐着恶话,没谁敢劝。
金子太是村子里威望最高的人,牛犟的人都会听金子太的。金子太拿出抽牛鞭子,狠狠地抽了升子爷几鞭子,抽得他丢下刺条子就跑,酒也醒了一半。几个嫂子赶快给秀婆披了上衣,松了绳子。秀婆进了屋,拿起一瓶药就往嘴里倒。“哈了,秀子喝药了!”几个嫂子,掰开秀婆的手,攥着给猪娃治虱子的敌百虫药瓶子,慌得大伙赶紧救。酒醒的升子爷,跪在秀婆面前,说:“媳妇,你吞了几片?赶快吐啊。”秀婆不吐,把嘴咬得死死的。升子爷一声断吼:“用筷子撬,拿尿罐子来!”七手八脚,摁的摁,掰的掰,撬的撬。升子爷刚刚把尿罐子凑到秀婆嘴边,“哇”一声,秀婆吐了。升子爷满地下找药片,找到了八片。问秀婆:“还有几片?”秀婆的舌头被筷子压着,说不出,腾出一只手,比个二字。“灌尿!”升子爷又一声断吼。“哇”,两片吐出来了。
升子爷领着秀婆,迈着碎步,去老街了,准备给秀婆买衣服,顺便咥一盘五里蒸面。
村子里的路,组组通了。去阴沟,也是宽阔的水泥路。在路上,我遇到了半语子烈子爷。烈子爷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了,他跟哥嫂一起生活,大集体的时候,烈子爷一身好力气,在生产队里,是挣工分的高手,担尿,挑粪,抬石头,他挣得工分最多,他喜欢给人帮忙,我父亲是教师,远离他乡教书,我们人小,母亲力气小,晚上生产队分粮食,都是烈子爷给我们挑的。梅子是个寡妇,烈子爷偷空给她家挑水,让单身的狗子爷狠狠揍了一顿,揍掉了一颗门牙。原来,狗子爷暗恋梅子,只是背着人偷偷给梅子挑水、劈柴、砸碳。挨了打的烈子爷,从那以后不敢给梅子家干活了。如今,烈子爷的哥嫂去世了,侄儿在外打工,屋里留下他一人,他吃着低保,享受着护理费,村上本来安排他去养老中心,他死活不去,用疙疙瘩瘩的半语子话说:“自己还挪的动,不给国家找麻烦。”他养了一头猪,上坡给猪剜草。
烈子爷认出我,羞羞答答喊出我的小名,不停地给我竖大拇指,暖流在我的周身流淌。我给烈子爷敬一支香烟,点上,他猛猛吸一口,笑了。
长梁串联着东西走向的几匹山梁,二麻沟、阴沟、柿树碥、尹家坡,这些沟沟砭砭,过去都荒芜着,成了野鸡出没,狐走兔跳的地方,复员军人堂弟,拿他打工挣来的第一桶金,承包了荒山野岭,植了桑树,盖起了养蚕工厂,带领村民在原地发家致富。
我的父母,就埋葬在我家的承包地阴沟,围绕坟周围是柏树,叶子翠绿,在枯草中更加苍劲。前面是一方塘,清水可鉴,水波微微,方塘里,十几只野鸭游曳,弄出涟漪几许。冬天里,其他花都凋零了,有一种野菊花还在开放,白色球状绒花,密密麻麻,绽放在枝头,为枯黄的野岭点燃一盏盏亮灯,这种野菊花的学名叫千里光,它们一同陪伴着我的父亲母亲。一棵苦楝树长在坟上,小小的苦楝树,结着一嘟噜一嘟噜苦楝蛋,金黄色的小果实,轻轻晃动。苦了一辈子的父亲母亲,还在结着苦苦的果子么?给他们烧纸、上香、磕头,然后陪他们坐坐。我是不抽烟的,今天带了一包中华烟,只给烈子爷敬一支,我取一支,点燃,递给父亲,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陪父亲抽。青烟袅袅里,我看到父亲抽得很香。父亲一辈子没抽过中华烟,他备课、思考问题,是要抽烟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抽六分钱的《经济》,基本上是半个月一包子。七十年代,抽九分钱的《羊群》。八十年代抽两毛钱的《宝成》。直到二十世纪才抽上两块钱左右的香烟。我们都给父亲买的好烟,他舍不得抽,拿到代销点换成低档的烟抽。二弟给他的两包中华烟,硬是舍不得抽,直到父亲去世,箱子底下翻出这两包烟,已经发霉了。小时候,不懂事的我们,埋怨父亲母亲没给我们留下丰厚的财产,回想起来,真后悔。父亲母亲教我们做人,培养我们上了中专和大学,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看看我们长大了,饭量增了,父亲申请调回本村教书。民办教师的父亲,一个月只有六块钱,咋养活我们?回村教书的父亲,白天上课,晚上和母亲一起做挂对子,那时候谁家房屋落成恭喜,就是送挂对,一副挂对两块钱。每到腊月间,父亲放假了,就开始写春联,我们拿到集镇上卖春联。做挂对、写春联,让我们度过了荒年,培养我们都走上了社会。翻阅了父亲留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里夹着一份契约,我父亲买了强爷的半边堂屋和一间庄基地,付费二百三十元整,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这个钱数,不知在当今能换算多少钱?但是,我知道,在当时,一枚鸡蛋一分钱、一斤大米八分钱、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折算一个劳动日)一角五分钱,按照劳动日折算,要一千五百三十多个劳动日、四年多的劳动时间啊。
家乡的新路是沿河边修的,新村也在新路边兴起,一家挨一家的楼形态各异。河东河西,都是抓一把捏出油的肥沃土地,过去没人耕种。山爹是退伍军人,他的战友高薪聘请他做经理,他不去,留在家乡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他引进了中国农科院培育的甘蔗新品种——脆蜜蔗1号,通过试验种植50亩,结果成功了,两委会一商量,提出了:‘南蔗北移、甜蜜产业、甜美生活’的集体产业发展思路。今年,小河两岸的沙土田300亩都种植成甘蔗,每亩给咱农户地租1000元,加上父老乡亲们种甘蔗、浇甘蔗、砍甘蔗等劳务费每人每天100元收入,收入可观。成立了甘蔗种植农民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为农户提供种子和技术支持,除去成本和费用,利润都分红给乡亲们,真正让咱们乡亲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河两岸的甘蔗收割完了,剥了叶,扎了捆,等待进入河东边的甘蔗酒酿造厂。在过河东的小桥上,遇到了运甘蔗的宝爹,宝爹说:“侄儿子,咱村大有希望,长梁是桑园林,大坡梁是桃树园,川道是甘蔗林,外出打工的都朝回赶,来家门口挣钱啊!甜蜜的日子就在跟前呀!”宝爹哈哈大笑着,这一笑,惊飞了河里的几只白鹭,它们朝鲤鱼山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