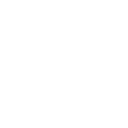再读流沙河

新华社成都11月23日电(记者 童芳)记者23日从四川省作协获悉,我国现代诗人、作家、学者流沙河于23日下午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8岁。
流沙河女儿给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发短信确认,流沙河于23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去世,走得很平静。
流沙河,本名余勋坦,1931年出生于成都,故乡四川金堂。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主要作品有《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谈诗》《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诗话》《锯齿啮痕录》《庄子现代版》《流沙河随笔》《Y先生语录》《流沙河短文》《流沙河近作》等。诗作《就是那一只蟋蟀》《理想》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迄今为止,已出版小说、诗歌、诗论、散文、翻译小说、研究专著等著作22种。
黄舟山
11月23日下午,流沙河先生走完了88个春秋,离开了我们,国内外多家媒体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一沉重的消息。这样一位文学大师于我来说,意义非凡,除了沉痛哀悼之外,我想把他的一些诗作和思想作一回望。
流沙河先生于1931年出生于成都市金堂县城,本名余勋坦。其主要作品有《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谈诗》《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诗话》《锯齿啮痕录》《庄子现代版》《流沙河随笔》《Y先生语录》《流沙河短文》《流沙河近作》等。诗作《就是那一只蟋蟀》《理想》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他以诗成名,对汉语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晚年转向古文字和古代典籍研究,卓然大家。艾青、臧克家、何其芳、郭小川等对他高度肯定。
我最早接触流沙河先生的作品是在安康师范学校读书时,他的诗作《理想》被收录到我们的《文选和写作》课程,至今感受深刻,虽然这首诗和今天的后朦胧派和后现代主义、先锋派诗作的笔法迥异,但不隐晦不矫揉造作,时时启迪着我、激励着我,彰显了明丽的愿景:“……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理想使忠厚者常遭不幸/理想使不幸者绝处逢生/平凡的人因有理想而伟大/有理想者就是一个‘大写的人’……理想开花,桃李要结甜果/理想抽芽,榆杨会有浓荫/请乘理想之马,挥鞭从此起程/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我被诗中充满哲理的诗句所打动、所震撼。在此之前,我对理想的概念十分模糊,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具体的还是遥远的,还是其他的什么。读了这首诗之后,顿时产生了拨云见日的感觉,我的理想渐渐地清晰了、明确了,要像流沙河先生那样,成为一个有理想不虚度年华的人!
流沙河先生是一个勤勉自律和感情真挚的人。1974年秋天他在故乡老家写下《贝壳》一诗:“曾经沧海的你/留下一只空壳/海云给你奇异的纹理/海月给你莹莹的珠光/放在耳边/我听见汹涌的波涛/放在枕边/我梦见自由的碧海。”当时文革十年浩劫,作者被劳改被流放被批斗被打成“右派”,用繁重的体力劳动剥夺了他的文学创作,但他理想之光不灭,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忙里偷闲,从中国古典文化汲取营养,不断充实自己的思想武库和文学功底,利用在图书馆当清洁工的闲暇时间,先后对《诗经》《楚辞》《说文解字》《古文观止》等文献,作了大量前瞻性的研究和解读,提出了一系列令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刮目相看的独到见解。
文革结束后,组织上没有抛弃他,1979年复出之后担任多家刊物的主编,尤其在担任《星星》诗刊期间,翻译并推介了大量的优秀诗作,1982年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风趣地对同志们谈起流沙河先生:“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这当然不仅仅指的是流沙河先生的诗作《就是那只蟋蟀》:“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而是乡愁的血脉相依,诗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和盼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他的一生干干净净,温暖从容。作为一个文人,特别是有才华的文人,一旦放纵自己失去底线,就会在世俗名利双收中毁掉自己的才华。流沙河后来当选为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多家媒体要求他搞些宣传个人的新闻发布会和作品推介会,都被他婉言谢绝。退休以后更是深居简出,但又绝不离群寡居,他尽量用自己的智慧温暖世界,把自己的知识无条件的传授给青年文学者,答疑解惑,探讨交心,不醉心于名利,不汲汲于富贵,他的文字和灵魂一样,都是干干净净的。流沙河始终保持着君子之风,适度批评但不流于尖酸,坚守价值但又遵循时变,因为他深知作为那只蟋蟀,在自己的田野里鸣唱,才是属于自己的歌声。
流沙河先生的历史审视和严谨治学的作风时时警醒着我们。虽然先生在退休后研究古文字,但在我们眼里这位于1989年挥别诗坛的老人首要身份还是诗人。
前不久,流沙河先生读到某位云南诗人的新作,“你们仔细看看这写的是什么?”老人很是不屑。“一切美好的诗歌都有秩序”,流沙河认为,诗歌的秩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一是意向;“意向的秩序更加艰难。优秀的诗人可以把常见的意向组合在一起,给人新鲜感和震撼”。流沙河把现代诗歌日趋冷落归咎于秩序的缺失: “我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把现代的一些观念、一些文学,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
“新诗永远不能替代古诗”,在和青年学者交流时看到大家踊跃发言,他很欣慰也很谦虚。他希望听众能通过自己的讲座懂得古诗。“经典只有懂了才有兴趣会去读,我无非是引起他们的兴趣。至于写诗,我从来不教,我自己都写不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先后读完他的《流沙河诗集》《台湾诗人十二家》《写诗十二课》等一系列作品集。面对他的书籍,我目不转睛,反复研读和思考,从而使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学到了很多技巧,受用无穷,我在宣传部门工作二十余年来,利用闲暇时间写诗二千余首、发表八百多首(件),每一次作品都一遍遍否定、一遍遍重新抒写,甚至付之一炬,这与我学习流沙河先生严谨治学治文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今天,面对他的离去,读着他的作品,我发现他的良心、品德和节操依然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他像一盏不灭的灯光,照耀着我们前行,他不仅属于四川,也属于文学、属于诗歌、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