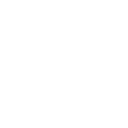那一间老屋,那一口老羊皮箱

□ 翁 军
每次回老屋,总是喜欢在楼上楼下转转。老家具还是老样子,纹丝不动,柜子落满了灰,打开抽屉,里面敞开一个塑料袋子,母亲的针头线脑和纽扣还在,柜子上面的电视机好长时间没人动过,罩子上印着红牡丹,远远望去,显得格外猩红。
一个角落放了几条凳子,堆了些杂物。在白昼光芒照射下,一口斑斓的旧皮箱,让我眼睛一亮。羊皮箱,这是姥姥当年陪嫁品,一个装满儿时记忆的“百宝箱”。
对老屋的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我赞同老屋是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家这种说法。我的老屋有两个,一个在紫阳县蒿坪镇,留下青葱的地方,房子早已荡然无存了。一个在安康老东关,房子还在,父母已不在了。岁月迁徙,物是人非,这一座红砖青瓦的楼房,前后历经了三十多年风风雨雨,沧桑依旧。父母都是老东关人,他们的老屋原本不在这里,但离这儿也不远。父亲的老屋与此比邻两条街,母亲的老屋距此东约100米,在安康老城门——朝阳门的脚下,1983年安康城遭遇特大洪水,二老的老屋均被摧毁,当时他们在外地工作,房没了人幸免,父亲的老屋让他兄弟在原址重建了,母亲的老屋被扩建城堤征用了。于是,在亲戚的撮合下,东拼西借凑了一点钱购买了此房。这条街叫石坊街,这条巷是无名巷,老屋就在巷道曲径通幽的最深处。
父亲性格刚烈,母亲却是个温柔似水的人,羊皮箱就是姥姥留给母亲的。姥姥姓马,是个小脚女子。姥爷姓刘,是老东关的大户人家,据说他父亲的父亲是晚清举人,威风而低调,我以前很懵懂,人云亦云,没有探究,我现在很懊悔,时过境迁,无法考证。不过从母亲名字叫“珺珉”判断,她家应该是有学识的。母亲一辈子不和任何人计较,很贤惠、很优雅、很和蔼,从不抱怨什么,生前很少跟我们谈家境的事情。
似乎,这一口羊皮箱在默默诉说剪藏的时光。姥姥守寡的早,母亲是她唯一的依靠,母亲工作到哪,姥姥就跟随在那儿。记得还在蒿坪小镇,每天上学,姥姥把我拉到床前,打开枕头边的这口羊皮箱,掏出核桃、花生、板栗什么的,塞在我裤兜里。每天放学,我背着书包回家第一件事找姥姥,要玩一下羊皮箱里的“宝贝”。羊皮箱里的“宝贝”真不少,装在一个黝黑锃亮的月亮盒里,藏有簪头、玉佩、玛瑙、项链什么的“细软”,母亲说姥爷娶姥姥时,是用八抬大轿抬进门的。水灾前,朝阳门的老屋木楼上还有银饰凤冠和宝剑,不知道是“水”收了,还是“人”丢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听母亲讲的家史。
四十年前,姥姥油光的羊皮箱,装着我童年的渴望和梦想。四十年后,再睹这几乎被遗忘的老皮箱,破旧、斑驳,沉淀了数不尽的忧伤……羊皮箱出城,姥姥留在了他乡,羊皮箱回城,盛载了清贫和其乐融融一段时光,母亲和父亲在厮守金婚诺言中撒手离去,留下了空候的苍白,不知不觉一晃十年,期间一位哥哥也“掉队”了……五指连心的弟兄,我们几乎崩塌了精神殿堂。
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姥姥最疼我,哥哥们迁就我。从小到大,我受到家人千宠百爱的呵护,几十年过去了,在家人的眼里“我”还是被保护对象。在父母的教诲下,我们弟兄、妯娌间从不红脸从不争执,孩子们以年龄大小排序,大女莎莎、二女倩倩、三女潇潇、四女琪瑶、五女羽蓉、六儿瀚尧,两个小外孙宸烨和若凡,亲兄妹般……大家都买了商品房,我也从拥挤的江南搬到了江北新居。
过年时,嫂子做了一个象征团圆的“紫阳蒸盆子”, 物华天宝,热气腾腾,在孩子们欢颜中,我们品尝着曾经的味道。
渐行渐远的青春,心绪常常像羊皮箱一样,空荡荡的。唯有逗留老屋,哪怕是一小会儿,找趣抚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