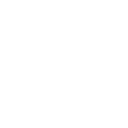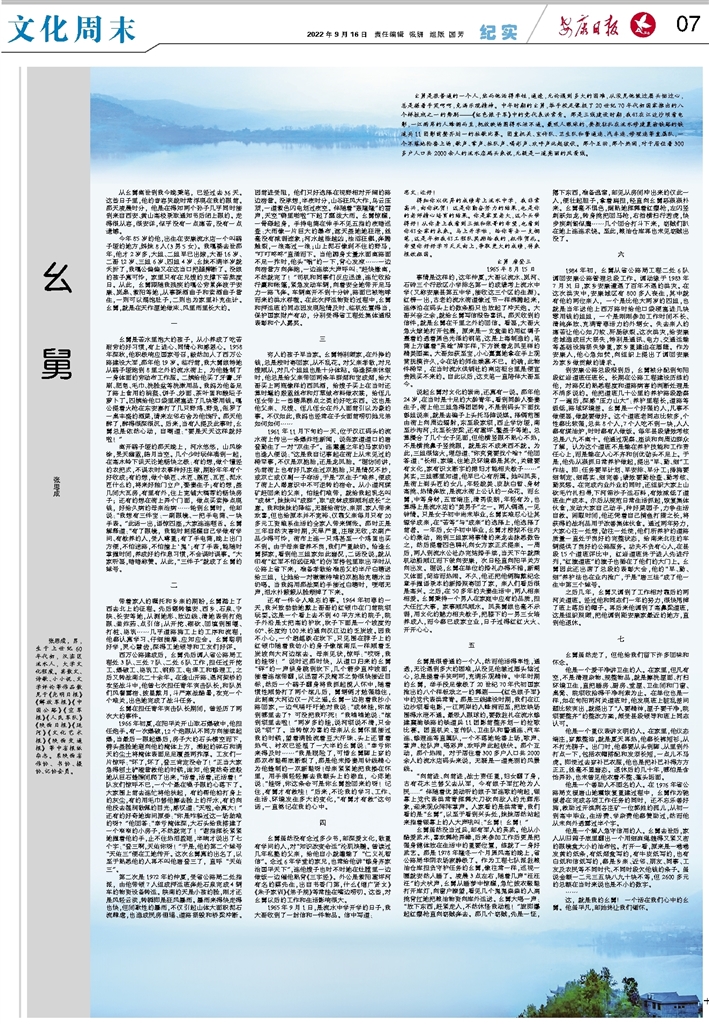幺 舅
张思成
张思成,男,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汉滨区流水人,大学文化程度。其散文、诗歌、小小说、文学评论等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公路》《空军报》《人民军队》《陕西日报》《延河》《文化艺术报》《陕西交通报》等中省报纸杂志。系陕西省作协、书协、摄协、记协会员。
幺舅是很普通的一个人,然而他活得率性,通透,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从没见他皱过眉头恼过心,总是搓着手笑呵呵,充满乐观精神。中年时期的幺舅,举手投足像极了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推出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那是三线建设时期,我们在江边沙坝看电影,一江两岸的人蜂拥而至,把放映场围得水泄不通。最吸人眼球的,要数驻扎在流水修建襄渝铁路的铁道兵11团影前整齐划一的拉歌比赛。团直机关、宣传队、卫生队和警通连、汽车连、修理连等直属队,一个不落地轮番上场,歌声、掌声、拉队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那个互动,那个热闹,对于居住着300多户人口共2000余人的流水店码头来说,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幺舅离世到我今晚秉笔,已经过去36天。这些日子里,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天凌晨时分,他是在得知两个孙子几乎同时接到来自西安、黄山高校录取通知书后闭上眼的。走得很从容,很安详,似乎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点遗憾。
今年85岁的他,出生在安康流水店一个叫鹞子垭的地方,姊妹8人(3男5女)。我嘎婆去世那年,他才2岁多,大姐、二姐早已出嫁,大哥16岁、二哥12岁、三姐6岁、四姐4岁、幺妹不满半岁就夭折了,我嘎公偏偏又在这当口把腿摔断了。没娘的孩子真可怜,家里只有在兄嫂的支撑下苦熬度日。从此,幺舅跟随我残疾的嘎公劳累奔波于安康、岚皋、紫阳等地,从事踩酒曲子和卖酒曲子营生,一则可以混饱肚子,二则也为家里补充生计。幺舅,就是在天作屋地做床、风里雨里长大的。
一
幺舅是苦水里泡大的孩子,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有上进心、同情心和感恩心。1958年深秋,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加入了西万公路建设大军,那年他19岁。临行前,我大舅娘特地从鹞子垭跑到8里之外的流水街上,为他缝制了一身体面的劳动布工作服。二姨给他买了牙膏、牙刷、肥皂、毛巾、洗脸盆等洗漱用品。我妈为他备足了路上食用的锅盔、饼子、炒面、茶叶蛋和酸坛子萝卜丁。四姨给他口袋里硬塞进了几块零用钱。嘎公提着火枪在东安寨打了几只野鸡、野兔,张罗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请来左邻右舍为他饯行。那天他醉了,醉得很深很沉。后来,当有人提及此事时,幺舅总是依然心动,自嘲道:“要是天天这样就好啦!”
离开鹞子垭的那天晚上,河水悠悠,山风徐徐,旻天幽蓝,皓月当空。几个少时玩伴凑到一起,在高木岭下谈天论地畅快之极:有的想,做个懂经的农把式,不误农时农事种好庄稼,期盼年年有个好收成;有的想,做个铁匠、木匠、篾匠、瓦匠、泥水匠什么的,将来好独门立户,娶妻生子;有的想,盖几间大瓦房,有里有外,住上宽铺大稿荐的畅快房子;还有的想在街上弄个门面,做点买卖挣点现钱,好给久病的母亲治病……轮到幺舅时,他却说:“我想有三件宝:一副眼镜、一把手电筒、一块手表。”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大家连连咂舌。幺舅解释道:“有了眼镜,我能时刻提醒自己学做有学问、有教养的人,受人尊重;有了手电筒,晚上出门方便,不怕迷路,不怕撞上‘鬼’;有了手表,能随时掌握时间,养成好的作息习惯,不会误时误事。”大家听罢,暗暗称赞。从此,“三件子”就成了幺舅的绰号。
二
带着家人的嘱托和乡亲的期盼,幺舅踏上了西去北上的征程。先后辗转镇安、西乡、石泉、宁陕、长安等地,从测地形、放边线、清地表到打炮眼、装炸药、点引信;从开挖、砌砍、回填到围堰、打桩、浇筑……几乎道路施工上的工序和流程,他都认真学习、仔细揣摩、应知应会。幺舅聪明好学,灵心慧齿,深得工地领导和工友们好评。
西万公路建成后,幺舅先后调入省公路局工程处3队、三处7队、二处6队工作,担任过开挖工、爆破工、浇筑工、钢筋工、电焊工和修理工,之后又转战南北二十余年。在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攻坚战斗中,他曾七次担任青年突击队长,和队员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斗严寒战酷暑,攻克一个个难关,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幺舅在担任青年突击队长期间,曾经历了两次大的事件。
1966年初夏,在阳平关开山取石爆破中,他担任炮手。有一次爆破,12个炮眼从不同方向接续起爆,当最后一眼起爆后,房子大的石头横空而下,劈头盖脸地砸向他的掩体上方,溅起的碎石和满天的尘土将掩体表面足足覆盖两拃厚。工友们一片惊呼:“坏了,坏了,登三肯定没命了!”正当大家急得刨土铲碴营救他的时候,谁知,他竟然奇迹般地从巨石缝隙间爬了出来,“活着,活着,还活着!”队友们惊呼不已,一个个悬在嗓子眼的心落下了。大家围上前去连忙将他扶起,有的帮他拍打身上的灰尘,有的用毛巾替他擦去脸上的汗水,有的向他投去温润敬佩的目光,感叹道:“天啦,命真大!”还有的好奇地询问原委:“你是咋躲过这一场劫难的呀?”他回答:“幸亏掩体深,大石头给我搭建了一个窄窄的小房子,不然就完了!”谢指挥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止不住热泪盈眶,半晌才说出了七个字:“登三啊,天佑你呀!”于是,他的第二个绰号“天佑三”便在工地传开。这次幺舅真的出名了,以至于熟悉他的人再不叫他唐登三了,直呼“天佑三”。
第二次是1972年的仲夏,受省公路局二处指派,由他带领7人组成押运班奔赴石泉完成4辆车的物资设备转运。陕南的天是小孩的脸,刚才还是风轻云淡,转瞬即是狂风暴雨。暴雨来得快走得也快,但间歇性的暴雨,不仅引起山体大面积泥石流肆虐,也造成民房倒塌、道路损毁和桥梁冲断。因前进受阻,他们只好选择在视野相对开阔的路边宿营。没承想,半夜时分,山谷狂风大作,乌云压顶,一道紫色闪电划过夜空。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天空“噼里啪啦”下起了瓢泼大雨。幺舅惊醒,一骨碌起身,手持电筒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暗巡查:大雨像一片巨大的瀑布,遮天盖地地狂泄,丝毫没有减弱迹象;河水越涨越凶,浊滔狂飙,奔腾触裂,一浪高过一浪;山上泥石像刹不住的野马,“叮叮咚咚”直涌而下。当他蹲身丈量水面离路面不足一拃时,他头“嗡”的一下,背心发凉……一边向宿营方向奔跑,一边连续大声呼叫:“赶快撤离,不然就完了!”司机和同事们反应迅速,连忙收拾行囊和帐篷,紧急发动车辆,向着安全地带开足马力一路飞奔。车辆离开不到十分钟,路面已被咆哮而来的洪水吞噬。在此次押运物资的过程中,幺舅和押运班的同志因发现险情及时、临机处置得当,保护国家财产有功,分别受得省工程处集体通报表彰和个人嘉奖。
三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幺舅特别顾家,在外挣的钱,总是按时寄回家,从不乱花。对父亲孝敬,对兄嫂顺从,对几个姐姐也是十分体贴。每逢探亲休假时,他总是给父亲带回两条羊群烟和宝成烟,给大哥买上两瓶像样的西凤酒,给嫂子买上在当时还算时髦的殷蓝丝布和灯草绒布料做衣裳,给侄儿侄女带上一些糖果糕点之类的好吃东西。这也是他父亲、兄嫂、侄儿侄女在外人面前引以为豪的事。不仅如此,我妈也经常在子女面前唠叨她兄弟如何如何……
1961年11月下旬的一天,位于汉江码头的流水街上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说张家道道口的唐登勤生了一对“双生子”。连耄耋之年的马家奶奶也逢人便说:“这是我自记事起在街上从未见过的稀罕事,不仅是双胞胎,还是龙凤胎。”据坊间讲,先前街上也有好几家生过双胞胎,只是情况不妙,或双亡或仅剩一子存活,于是“双生子”难养,便成了街上人潜意识中不可逆转的宿命。从小道河煤矿赶回来的父亲,怕娃们难带,就给我起乳名叫“成林”,妹妹叫“成群”,取“成林成群顺利成长”之意。我和妹妹的降临,无疑给街坊、亲朋、家人带来欢喜,但也给原本并不宽裕、仅靠父亲每月只有20多元工资维系生活的全家人带来惆怅。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旱严重,庄稼无收,农副产品少得可怜,街市上连一只鸡甚至一个鸡蛋也买不到。由于母亲营养不良,我们严重缺奶。恰逢幺舅探家,看到他三姐家如此窘况,二话没说,就从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仿军挎包里取出平时从公路上省下来,准备孝敬给准岳父的半斤白糖送给三姐,让她给一对嗷嗷待哺的双胞胎充糖水当奶喝。当我妈用那战栗的手接过白糖时,哽咽无声,泪水扑簌簌从脸颊掉了下来。
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1964年初春的一天,我兴致勃勃地戴上哥哥的红领巾在门前院坝玩耍。这是一个看上去不到40平方米的院子,院子外沿是丈把高的护坎,坎子下面是一个坡度约60°、长度约100米的通向汉江边的乏炭坡。因我不小心,一个趔趄跌在坎下,只见围在脖子上的红领巾随着我幼小的身子像滚南瓜一样顺着乏炭坡向大河边滚去。母亲见状,惊呼:“哎呀,我的娃呀!”说时迟那时快,从道口归来的幺舅“砰”的一声纵身跳到坎下,几个箭步直冲坡面,接着连滚带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接近目标,然后一个鹞子翻身将我抓起揽入怀中,随着惯性顺势打了两个滚儿后,舅甥俩才勉强稳住,此刻离大河边仅一尺之遥。幺舅一边抱着我抄小路回家,一边气喘吁吁地对我说:“成林娃,你滚到哪里去了?可没把我吓死!”我喃喃地说:“滚到坝里去啦!”两岁多的娃,说河坝说不清,只会说“坝”了。当转惊为喜的母亲从幺舅怀里接过我的时候,望着满脸流着豆大汗珠、头上还冒着热气、衬衣已经湿了一大半的幺舅说:“幸亏你来得及时……”我是脱险了,可惜幺舅脚上穿的那双布鞋帮底断裂了,那是他未婚妻用针线精心为他缝制的一双新鞋呀!母亲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用手绢轻轻擦去我额头上的渗血,心疼地说:“娃呀,你这条命可是你幺舅捡回来的呀!记住,有舅才有救哇!”后来,不论我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发生多大的变化,“有舅才有救”这句话,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四
幺舅虽然没有念过多少书,却深爱文化,敬重有学问的人,对“知识改变命运”沦肌浃髓。曾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给他自小就灌输了“仁义礼智信”。念过6年学堂的家兄,也常给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他嫂子也时不时地在灶膛里一边做饭一边催他熟背《三字经》。外公是紫阳蒿坪河有名的蔡先生,出自书香门第,什么《增广贤文》《朱子家训》《弟子规》等常挂在嘴边唠叨。这些,对幺舅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影响很大。
1965年9月1日,是流水中学开学的日子,我大哥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件物品。信中写道:
思文:近好!
得知你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流水中学,我非常高兴,向你祝贺!这是你勤奋努力的结果,也是你的老师精心培育的结果。你是家里老大,这个头带得好!从你身上我看到三姐和张哥的希望,也看到你们全家的未来。马上开学啦,给你寄去一支钢笔,这是年初我们工程队奖励给我的,权作贺礼。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更大的成绩,将来报效祖国。
幺舅 唐登三
1965年8月15日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仲夏,大哥以流水、岚河、石砖三个行政区小学排名第一的成绩考上流水中学(又称安康县第五中学,接收这三个区的生源)。红榜一出,古老的流水街道像过节一样沸腾起来,连停泊在码头上的数条船只也放起了冲天炮。大哥兴奋之余,就给幺舅写信报告喜讯。那天收到的信件,就是幺舅在千里之外的回信。看罢,大哥火急火燎地打开包裹,原来是一支盒装的用红绸子裹着的透着黑色光泽的钢笔,这是上海制造的,笔筒上方镶着“英雄”牌字样,下方嵌着龙凤呈祥的精美图案。大哥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上观赏抚摸许久,令在场的师生羡慕不已。的确,此物件稀罕,在当时流水供销社的商店柜台里是便宜贵贱买不来的。自此以后,这支笔一直陪伴大哥至今。
说起幺舅对文化的崇尚,还真有一说。那年他24岁,在当时是十足的大龄青年。看到同龄人娶妻生子,街上他三姐急得团团转,不是到码头下面找彭姐说亲,就是去碥子上头托马婶说媒。择偶范围由街上向周边辐射,东至段家坝,西止学坊垭,南至沙沟河,北至长安梁,还有蒿坪、鳖盖子等地。总算撮合了几个女子见面,但他横竖眼不熟心不热,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就是东不成来西不就。为此,三姐很恼火,埋怨道:“你究竟要找个啥?”他回答道:“长相、家境、住地及环境都是其次,关键要有文化,家有识文断字的媳妇才能相夫教子……”其实,三姐哪里知道,他早已心有所属。她叫凤英,是街上剃头匠的女儿,年轻貌美、皮肤白皙、身材高挑、热情奔放,是流水街上公认的一朵花。而幺舅,中等身材,五官端庄,清秀俊朗,年轻有为,也算得上是流水店的“美男子”之一。两人偶遇,一见钟情。只是女子初中尚未毕业,幺舅实难忍心让其辍学成亲,在“苦等”与“成亲”的选择上,他选择了前者。一年后,女子初中毕业,幺舅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跑到三姐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悉数告之,然后提着四色聘礼向女方家正式提亲。一周后,两人到流水公社办完结婚手续,当天下午就乘机动船顺江而下驶向安康,次日径直向阳平关方向出发。据说,幺舅在单位的婚礼办得不错,新潮又体面,简洁而热闹。不久,他还把他俩胸戴纪念章手握语录本的新婚照寄回了家,亲人们看后很是高兴。之后,在50多年的夫妻生活中,两人相亲相爱。幺舅秉持一个男人在家庭中应有的品质,担大任扛大事,家事顺风顺水。凤英舅娘也毫不示弱,用文化的魅力相夫教子,把膝下的一男三女培养成人,而今都已成家立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开开心心。
五
幺舅是很普通的一个人,然而他活得率性,通透,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从没见他皱过眉头恼过心,总是搓着手笑呵呵,充满乐观精神。中年时期的幺舅,举手投足像极了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推出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那是三线建设时期,我们在江边沙坝看电影,一江两岸的人蜂拥而至,把放映场围得水泄不通。最吸人眼球的,要数驻扎在流水修建襄渝铁路的铁道兵11团影前整齐划一的拉歌比赛。团直机关、宣传队、卫生队和警通连、汽车连、修理连等直属队,一个不落地轮番上场,歌声、掌声、拉队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那个互动,那个热闹,对于居住着300多户人口共2000余人的流水店码头来说,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责任重,妇女翻了身,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伴随着优美动听的娘子军连歌的响起,银幕上党代表洪常青挥舞大刀砍向敌人的光辉形象,迎来观众阵阵掌声。人家看的是洪常青,我们看的是“幺舅”,以至于看到兴头处,妹妹居然站起来指着银幕上的人大声吼叫:“幺舅!幺舅!”
幺舅虽然没当过兵,却有军人的英武。他从小酷爱武术,喜欢舞枪弄棒,后来参加工作后更是把强身健体放在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练就了一身好武艺。那是1978年隆冬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省公路局华阴农场寂静极了。作为工程七队派驻粮油仓库担负守护任务的幺舅,像往常一样,巡视一圈就安然入睡了。凌晨3点左右,随着几声“汪汪汪”的犬吠声,幺舅从睡梦中惊醒,急忙披衣靸鞋打开库灯,向窗户瞭望,看见几个鬼鬼祟祟的人肩挑背扛地把粮油物资向库外运送。幺舅大喝一声:“放下东西,赶紧走人,不然休怪我动粗!”旋即攥起红缨枪直向窃贼奔去。那几个窃贼,先是一怔,撂下东西,准备逃窜,却见从房间冲出来的仅此一人,便壮起胆子,拿着扁担,径直向幺舅恶狠狠扑来。幺舅毫不惧色,娴熟地挥舞着红缨枪,左闪竖刺跃如龙,转身挑把回马枪,右挡横扫行若虎,快步疾刺匐似鹰……几个回合打斗下来,窃贼们趴在地上连连求饶。至此,粮油仓库再也未见窃贼出没了。
六
1984年初,幺舅从省公路局工程二处6队调回安康公路管理总段工作。调动缘于1983年7月31日,家乡安康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在这次洪灾中,安康城区有800多人丧生,其中就有他的两位亲人,一个是比他大两岁的四姐,也就是当年送他上西万路时给他口袋硬塞进几块零用钱的姐姐,一个是刚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清纯奔放、充满青春活力的外甥女。失去亲人的痛苦让他心如刀绞、肝肠欲裂。这次洪灾,给安康老城造成巨大损失,特别是通讯、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损失惨重,家乡重建迫在眉睫。作为安康人,他心急如焚,向组织上提出了调回安康为家乡做贡献的请求。
到安康公路总段报到后,幺舅被分配到旬阳段红岩道班任班长。长期在公路工程建设历练的他,对路况的熟悉程度和道路病害的判断处理是不消多说的。他把道班几十公里的养护路段勘察了一遍后,深感“压力山大”:养护里程长,道路等级低,路域环境差。幺舅是一个好强的人,凡事不做便罢,做就要做好。这个道班老同志比较多,个性都比较强,总共8个人,7个人吃不到一块,人人都有煤油炉,时时都有人做饭。每年县段绩效考核总是八九不离十。他通过观察、座谈和向周边群众了解,认为这个道班不是输在养护技能和工作责任心上,而是输在人心不齐和创优劲头不足上。于是,他先从狠抓日常养护做起,提出“早、勤、细”工作法。即:任务要早计划、早安排、早分工;措施要细制定、细落实、细完善;绩效要勤检查、勤考核、勤奖惩。在完成内业外业的同时,还组织大家上山砍毛竹扎扫帚,下河筛沙子运石料,有效减低了道班生产成本。尔后从规范日常生活抓起,恢复集体伙食,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种好菜园子,力争生活自救。闲暇时间,他还凭着自己捕鱼打猎之长,将获得的战利品用于改善集体伙食。通过两年努力,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他们所养护的道路质量一直处于良好的完整状态,给南来北往的车辆提供了良好的公路服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县段15个道班评比中,红岩道班终于进入先进行列,“红旗道班”的旗子也插在了他们的大门上。幺舅因此还出席了总段的表彰大会,他的“早、勤、细”养护法也在业内推广,于是“唐三法”成了他一生中第三个绰号。
之后几年,幺舅又调到了工作相对靠后的两河关道班。经过他和同志们一年的努力,很快甩掉了班上落后的帽子。再后来他调到了高鼻梁道班,这是组织照顾,把他调到距安康家最近的地方,直到他退休。
七
幺舅虽然走了,但他给我们留下许多回味和怀念。
他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在家里,但凡有空,不是清理杂物、规整物品,就是擦洗屋面、打扫环境卫生,直把睡房、厨房、堂屋、卫生间和门窗、桌凳、院坝收拾得干净利索为止。在单位也是一样,如在旬阳两河关道班时,他发现班上脏乱差问题比较突出,就提出了“人要精神,屋子要干净,院坝要整齐”的整改方案,颇受县段领导和班上同志认可。
他是一个重仪表讲文明的人。在家里,他仪态端庄,穿戴整洁,就是夏天再热,他都长裤短衫,从不打光膀子。出门时,他都要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点一下,包括衣帽搭配和发须长短,一点儿不马虎。即使过去穿补巴衣服,他也是把补巴补得方方正正,丝毫不显窘态。退休后的几十年,哪怕是含饴弄孙,也未曾见他衣着不整、蓬头垢面。
他是一个善助人不图名的人。在1976年省公路局支援唐山地震恢复重建过程中,幺舅作为驰援者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还不忘乐善好施,救助过开滦荆各庄矿一位郭姓的孤儿,从初一到高中毕业,生活费、学杂费他都赞助过,然而他从未向外透露过半个字。
他是一个解人急守信用的人。幺舅去世后,家人从旧箱子底里翻出一个用细麻绳缠得又紧又密的眼镜盒大小的油布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卷卷发黄的纸条,有纸烟盒写的,有牛皮纸写的,也有白纸和信纸写的,都是乡亲、近邻、朋友、同事、工友及农民等不同时代、不同时段欠他钱的条子。虽说金额一二元三五块八九十块不等,但2600多元的总额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
……
这,就是我的幺舅! 一个活在我们心中的幺舅。他虽平凡,却始终让我们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