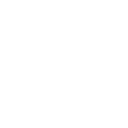那年 那山 那青春
赵云中
一个春暖花开的艳阳天,一位失联多年的老同学突然来访,我喜出望外,急匆匆奔到小区门口去迎接他。一见面如见亲人一般,紧紧握起他的手,撸着他的肩,快步走进小区,穿过弯曲的树荫花径,到达我家。落座未稳,就话语不停地聊个没完,却冷落了那两杯香气四溢的“女娲毛尖”。
长聊中,他聊出一段往事,挺惊险挺邪乎的。听得出,这段磨砺,磨出了他的坚强,磨出了他的韧劲,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也成就了他作为一名知名书画家的修为。
他神情投入地讲述了以下经历:
一、风雨滚子坡
寒窗多年熬到头,1958年毕业了,分配了。刚刚走出校门,就险象环生,预示了我这一生的不顺利。
告别母校,背上行囊,出发不远,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跋山涉水。第二天竟遇上了瓢泼大雨,天公出马对我进行无情的鞭打。为了显示自己的坚强,我没有住店歇脚,而是冒雨继续前行。第三天情况更为恶劣,在陡峭的“滚子坡”下的羊肠小路上,遭遇到了可怕的泥石流。我的双腿被陡坡上倾泻而下的厚厚的泥浆死死地焊住,动弹不得。眼见坡顶又有滚石泥浆哗哗而下,生命危在旦夕,此时,不知从何处猛生出拔山填海的力量,拼命拽动双腿,几步冲突出去,逃得一条性命。回首望山庆幸,看浑身上下是汗是水是泥浆,变成了活脱脱的一尊“秦俑”。
如此瘸瘸拐拐五天,终于到达那个堪称世上最小的山谷县城,分配到了文化馆,开启了一名在册的国家干部的正式生涯。
二、历险九弯子
深秋,接县府通知,叫我同县医院的一位黄姓医生一道去那更遥远更偏僻的平溪河大队搞“三秋”工作。
我二话没说,欣然领命。
一个晴朗的秋日,我们动身。可我们不认识路径,走向何方呢?只好机械地照着县长的叮嘱,顺着河边,循着电杆行走。逢了岔道,找人打问;左右无人烟可寻时,便扯了嗓门哟嗬:“到平溪河怎么走啊?”无人回应,只有四山嘲笑似的模仿我们的高嗓门儿回道:“到平溪河怎么走啊?”逗得我俩开怀大笑。无奈何,只得依照老谱,顺着电杆走。有时错了,就折回来,寻寻觅觅方才走上正路。
黄昏时分,我们到了一所小而又小的学校,叫作“双坪普小”,意外邂逅了一位比我高一级的同学,好像姓刘,在这里既当校长又当老师又当炊事员,大有他乡遇故知的喜出望外。他也欣喜有加,即令妻子为我们备膳。暮色中,炊烟升起,衬着千山,衬着林莽,衬着晩霞,构成一幅天然的彩墨山水画。须臾,酒菜端上,就在院坝间,在这画中,我们对酌,闲聊,海阔天空,无边无涯,尽情尽兴。
新月一镰,托在山巅,朦胧的清辉,香粉一般扑了我们的脸,张张清白。刘老师忽指黄医生的脸说:“你的脸怎么没有血色?”黄医生一惊,来回望了我和刘老师片刻,旋即爆出大笑,说道:“一样一样,都无血色。”我和刘老师对视,果然一样,遂一起开心地哈哈哈起来。
刘老师说,此去平溪河还有四五十里地,前面有个“九湾子”,古木参天,长草没膝,十分阴森,时有虫蛇出没,若逢阴雨天,狂风大作,龙吟蛟吼,海碗粗细的蟒蛇掀起草浪,追赶行人,十分可怖。说得我俩毛骨悚然。
蚊子在耳边嗡嗡嘤嘤,我啪的一声向后脑勺打去,清脆一响,稍稍为自己壮了壮胆。
刘老师说,“九弯子”再前,有一个“蚂蟥坡”,树干上,草丛间,全是旱蚂蟥。行人走过,即吸附在双脚双腿上,嗜血如饥似渴,要人命呢。你们千万小心!听了,我立起一身鸡皮疙瘩,心里叫苦不迭。
还有,山里正闹野人,出入民宅,偷鸡摸狗,抢吃抢喝……留下一双双硕大的脚印。那年月,全民忙着大炼钢铁,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野人自然趁虚而入,一尺多长的苞谷棒子耷拉着挂在秸杆上,谁见谁爱,它能不趁火打劫吗?
有了刘老师这一番惊心动魄的描述,次日上路,我俩就提心吊胆,格外警惕,生怕遇上野人,遇上蟒蛇,遇上蚂蟥。到了“九弯子”,我们屏息敛气,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一步一探,千般小心。茅茅路在林间草丛弯来绕去,时有时无。松木水桶般粗细,撑着蓝天,托起白云,凉风沁沁,阴影娑娑,一派静谧,一派死寂。所好蟒蛇无踪,野人无影,蚂蟥匿迹。正庆幸间,忽听草丛哗啦一响,老黄一声惊叫,猛然后退,重重踩了我的脚,痛得钻心,也发出一声嗷叫。细看时,一条绿蛇已窜去好远,虚惊一场。待稍许平静,我就笑他“胆小如鼠”;他反讥我“胆大若猫”。情绪方才轻松起来。
踏上苔藓铺陈的石砌桥,观赏那茂竹瘦溪,我油然吟起辛弃疾的《西江月》词《夜行黄沙道中》末了两句:“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只可惜少了旧时茅店,韵味不足了。
日衔西山时,终于到达目的地——平溪河,好一个世外桃源!青山绿树环绕,茅舍星罗其间,溪流巨石相拥,挑逗欢闹躲闪,景色迷人,环境幽静,村民质朴。这儿“山高皇帝远”,虽邻四川小三峡,四川不管;也邻湖北神农架,湖北不问;名分归属陕西,但“八千里路云和月”,鞭长莫及,终年极少有干部大驾光临。所以,我们的出现,竟成了稀罕之物,似洋人一般引来了人们的围观,尤其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孩子们。
头顶缠了几匝老青布的大队长立即为我们安排好膳食。煎洋芋粑粑炒琥珀色的腊肉片子,是山里人待客必不可少的贵菜,吃起来不腻又过瘾。洋芋粑粑可非洋芋片片哦,它是用洋芋浸于水中,摩擦于笞笈、笊篱等糙物上,再经包袱挤压过滤,沉淀成粉,又以此粉加水搅成糊状,于锅中油煎如布帛,切一寸大小方块而成。还有一宗稀世珍肴,是将天粟米粉煎成耙子,切方块炒腊肉,其味更加美不胜言,入口难忘。主食差点,玉米发糕,苦荞耙耙,洋芋渣馍。上等的就数“面面饭”了。此饭系用苞谷糁掺水三遍,糁拌三遍,上笼或甑蒸三遍而成,极干细极散口,故称“面面饭”。主人常盛极高一碗,俗称“帽儿头”,呈于客人。吃法上有点讲究,若从四周吃起,必会掏空根基而崩坍散落碗外,惹人笑话。正确的吃法是由顶尖吃起,方保无虞。这是我们经嘲笑、指点后方才学会的。
住处确实窝囊。那时的民居,土墙草棚,油渣被子、草席等,自然不能给我们“享受”。大队长费尽心思,决定把大队小学(仅两间半大小)的大门撬开,叫我们住进那木板楼上。可怜见那楼上常年无人居住,无人打扫。自楼梯以上扬尘碰头,蛛网蒙面,霉腥气呛鼻。这且不说,唯那耗子大得吓人,多得吓人,胆大得吓人。我们点了蜡烛(那里人不知电为何物)坐在床边,高声说话,意在吓唬耗子。然而他们无所畏惧,依然大摇大摆在房梁、椽间、墙头穿梭。我们拍打桌面、床板,发出吼声,驱赶它们,它们置若罔闻。更有胆大的竟然跑到桌面上来,同我们“亲善”。
困乏极了,顾不了,就硬着头皮熄灯睡觉。哪里睡得着哟,时不时那个儿大如猫的耗子爬上床来骚扰,爬上脸上来亲吻,我们得随时同它们展开战斗。
不知何时,我已九分迷糊,隐约中听到有人呼唤我的名字,一声长一声短,期期艾艾的。在这深山野坳里,谁能知道我的名字呢?莫非,莫非真的有鬼?纵然有鬼,我年纪轻轻,未做任何亏心事,我怕你何干?常言道,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管他呢!不,不可能是鬼。那声音虽然懵懵,却真切。我壮了壮胆,再醒醒神,竖耳细听,哟,是他。我向床里一摸,没见了人。就惊慌地大喊,老黄他痛苦地应了一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你在哪里?”“我在楼下哟!”“你怎么跑到楼下去了?”“起夜,掉到楼下来了。”糟糕,我忽地撩开被子,摸黑下楼。在楼梯下面摸到了他。他尿湿了裤子,腿被摔折了。此刻像死尸一般沉。我怎么也拖不动他,咋能上楼呢?紧急中,就无所顾忌了。我一介书生竟似一条莽汉,一脚把楼梯旁那间老师卧室的门踢开了。幸好是一面竹笆门,一段铁丝扣,没有让我太费力。
我把他安置在床板上,上楼摸到蜡烛、火柴,点燃亮,安慰着他,等待天亮。
拂晓,我急火火找来大队长。他看了,摇头叹息一声说:“昨晚看到他的脸色就不对,果然……”打住后面的话改了口气,一边安慰,一边埋怨,也无可奈何,因为这里没有郞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山那边的双坪管理区,请赫赫有名的草药郎中李金山。然而,此去百把里山路,谁去呢?再说李先生不一定肯来啊。
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果敢地说:“我去双坪请李老先生,大队长找人扎个担架,把老黄往出抬,到半途的双坪普小为他医治。”我想,那里有我的同学,多少方便一些。
大队长同意了我的意见。
三、求助李郎中
半晌午,我上了路。因为昨夜一场暴风雨,河水猛涨,路被淹了,我只好绕山而行。行至暮色苍茫时,我发现前面走着一个人,赶紧追上去,与他搭伴。岂料,我快他快,我慢他慢,总追不上他。待绕过几个弯子后,那人竟无声地消失了。我被他引入荆棘丛中,迷了路。我焦急地前寻后觅,左冲右突,未见路的踪迹。我心发怵,头发麻,悲苦地想到“完了”。焦虑间,倏忽想起苏联作家奥斯特诺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年月是很容易想起他的),就壮起胆子鼓励自己,别慌别怕,勇敢沉着,像保尔那样坚强。我稳住神,仔细打量山向。是呀,是来时走的路,怎么会不见了呢?天色已暗,怕是撞见“鬼打墙”了。无望中,寻觅中,突然发现山下河边有户人家,炊烟袅袅,犬声汪汪,就如见到救星似的三步两步跳下了山。经打问,老妪说,路就在山上,一点不错,并且站在屋檐下,给我细细指点。我似是明白了,噢噢谢别。但上得山来,又是一塌糊涂,哪里有路?只见山影憧憧,归鸟投林,我的心愈发慌了,冷汗淋漓。心一横,冲出去!冲出去!一股邪劲涌上来,管它荆棘割脸,尖刺牵衣,藤蔓纠缠,一概顾不得了,逃生要紧。衣破了,肉绽了,全然无感觉。当我最终冲出那片荆棘林,寻着似有似无的茅茅路,驻足回首时,顿觉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还奢想,若有一把椅子坐坐,那就幸福到了顶点。
次日黄昏,按预定计划,我同大队长等一杆人马汇齐在双坪普小。
李金山,一个瘦削细高精力旺盛的老头,专医跌打损伤的草药郎中,又会“咒语”,在那一带山中颇有名望,医治这小小跌伤自然不在话下。一路上,他给我讲了好多关于草医、草药、“咒语”的事。对于草医草药我没有兴趣,单对“咒语”十分的好奇。然而,我越盘问他越卖关子,不肯道出个中奥秘。只说些不着头脑的话糊弄我。
“手术台”设在教室的课桌上,大有农村宰猪的架势。老黄被抬上桌面时有些紧张。李先生说,不碍事,不痒也不痛,一下就好。他吩咐,拿碗凉水来,我的同学刘老师就遵命捧来一碗凉水。他接过,稍稍镇静,闭目敛神,抖动起山羊胡子,口中念念有词。词毕,噙一口凉水噗地喷向老黄的大腿,放了碗,麻利捏弄,猛然间用力一扯一推,说声“好了!”继之敷以草药,手术完毕。老黄果然没有大呼小叫。
事后,我问老黄,李先生猛扯你大腿时,真不痛吗?他说真不痛。于是,我对李先生的“咒语”更添了几分好奇。当他下山时,我特地跟定了他,一路鞍前马后虔诚地求教“咒语”。他依然故作奥秘,“王顾左右而言他”。但也达成一项意向性协议:到他家去,取书给我一读。于是,我高兴得两脚生风。然而,该死,不知在哪个沟沟岔岔里又生鬼事,竟然走失了李老先生。面对苍苍大山,莽莽林海,哪里寻他去?无奈间,我像个蔫黄瓜似的怏怏回到县城,留下偌大一个遗憾,至今不知“咒”为何物?
老同学讲完上述经历,意犹未尽,但酒尽菜残茶凉时晚,就起身告别,依依不舍。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副他的书法大作赠我,我接过如获至宝,连连道谢!他遂又发话邀我,待到金秋时,“移驾”他府,在其菊园,赏菊品茗,接着聊。
届时兴许又有新故事。